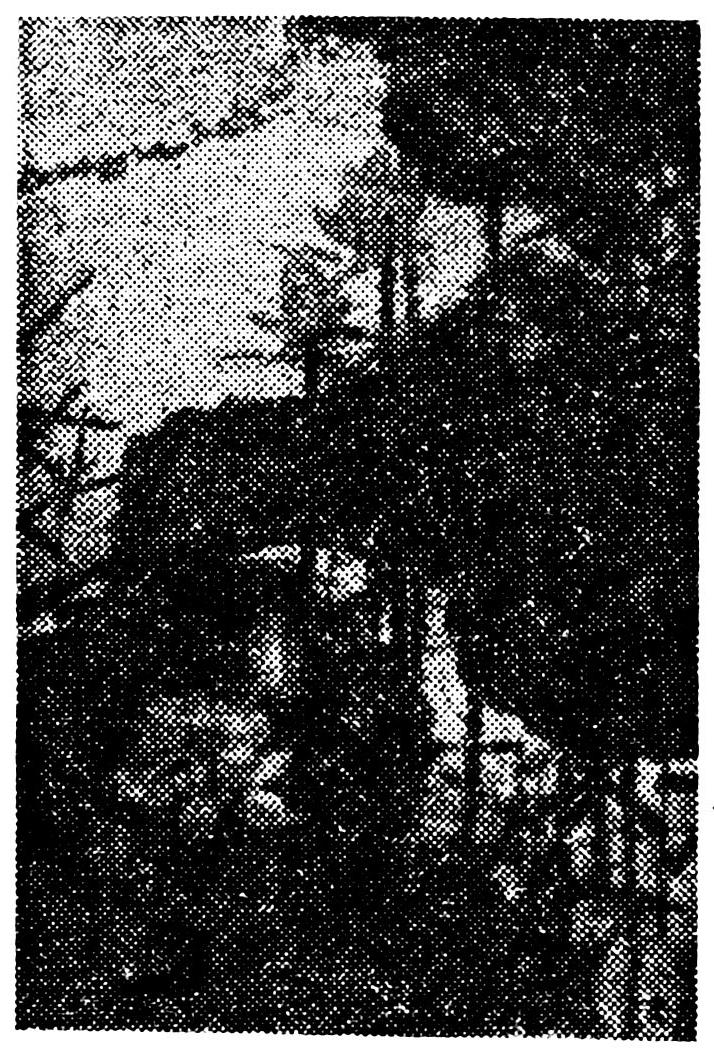萧霁 渔火
恩格斯说,文艺“要塑造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这里的“典型环境”,显然包括今天我们所说的典型的时代背景,典型的情节,典型的人物关系。小小说《扫大街的金霞》(载“陕西工人报”八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在这几方面都做出了一定成绩。
金碧辉煌的钟楼,衣着华丽的外国游客,笔挺西装,锃亮皮鞋的“中国小伙”……旁边,是一个扫大街的姑娘——金霞。她显得那样不起眼,不起眼到让那些媚外者认为微不足道,无怪乎那个前后追随着外国人换钢笔的小伙,轻蔑地说她“扫大街的”。可是,当她阻止了小伙子丧失国格的行动,对方在群众鄙夷的目光中低下头去的时候,人们看到,那个初看起来貌似“光彩”的人物变得暗淡起来,而貌似渺小的却显得伟大,浑身幅射着耀眼的光华。只有她——扫大街的金霞,才配站在这辉煌壮丽的钟楼下!
这里,假如作者选择的是一个工程师、教授、作家、领导干部——就是说,在世俗人们的眼里,是“有地位”的人,让他们来关心这件事情,作品也许不那么感人;而正因为主人翁的“不起眼”,才更有代表性。这大概就是作品在设置人物关系上的典型性。假如作品选择的时代不是随着开放政策带来某些人崇洋思想的今天,不是针对这一思想的事件,那么作品无疑也会失去一定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这又是作品在选择时代背景和情节上的典型性。
总之,不正是由于这几个方面的典型性,才使这篇不足七百字的小说,产生了如此摇动人们心魄的力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