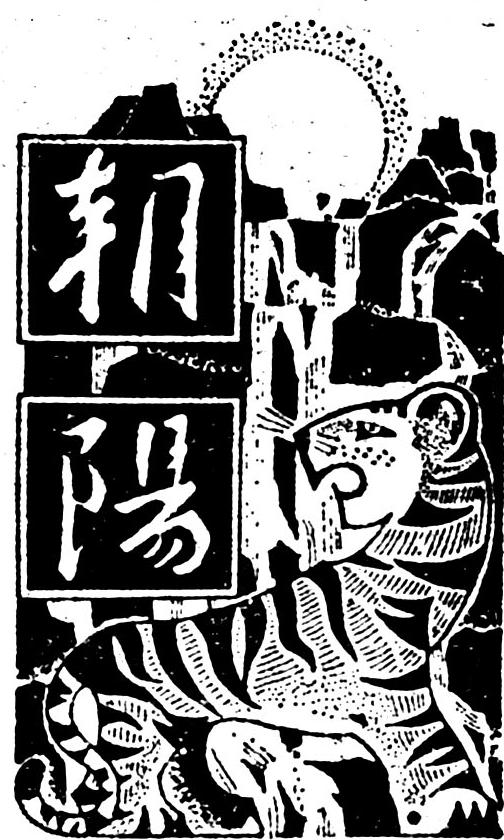王戈
初学写作,一般都要从自己的经历和身边的真人真事写起,比之那些生在北方写南方、长在城市写农村的异想天开的做法,这应当说是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途径。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有许多文学青年抱怨:我写的都是真的,生活中就是那么发生和发展的,为什么写出来反而不真实、不生动、不形象呢?
这几乎是搞创作的人都碰到过的苦恼。就我自己的体会,除了剪裁、概括、文字表达等技巧等方面的因素外,最重要的怕是感情凝聚得不够。现实生活中,确实不乏生动有趣的甚或离奇古怪的事情,但是文学艺术说到底是“情”的结晶,要以情动人。如果只满足于客观的描摹,哪怕再逼真,也满足不了人的审美感受。诉诸色彩的绘画尚且如此,诉诸文字的文学更是这样。借用一位美学家的话说,美是“有意味的形式”。何为“有意味”?就是有感情。人的审美感受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性的感官愉快,正在于其中包含有通过观念、想象凝聚出来的感情。文学创作,永能满足于生活现象一般意义上的观察、体验、感受,而要从特定的观念、想象去积淀、溶化,成为特定的审美感情。这种审美感情,包含有大量的观念和伦理,却又不能用简单的逻辑概念解释清楚,而成为一种不可用概念言说和穷尽表达的深层次反应。我们读贾平凹近期的一系列中篇,不正是有这种体味吗?“有意味的形式”,是说美在形式又不在形式,离开了形式(自然形体)固然没有美,而只有形式没有熔铸进去作者的审美感受也不成其为美。《天狗》、《人极》、《黑氏》等作品,恰恰美在流动于形式之外的“似与不似”之间。
创作上有“二度进入”一说。所谓“二度进入”,即通过对生活的直感,进入更深的层次,去挖掘生活的底蕴,揭示生活的真谛。没有这种功夫,创作很难上去。一九八二年我参加过一次高考招生工作,回来后写了两篇小说。一篇叫《九层台阶》,写一对夫妻为了孩子能录取,想方设法要见招生人员一面。见到了,作出许多阿谀奉承之事。孩子被录取了,但当俩口子大摆宴席准备款待时,招生人员早已离开了那个城市。这是从真人真事中演绎出来的二篇小说,浅层次地理解,表达了“鞭挞不正之风”这一类主题,发表后却没有多大反响。为什么取之于现实生活而又直接针贬时弊的反而无声无息?事后总结,当时只停留在对事件的客观描摹上,唯恐这一有趣的情节忘掉,急忙落笔成篇,思想上没有“二度进入”,没有凝聚出“有意味”的东西。距离太近,没有经过积淀的过程。紧接着,又写了《树上的鸟儿》,灵感是从一份考生档案上激发起来的,写出来却没有一丝真人真事的痕迹。有许多青年朋友以为我在学校,写的是真人真事,其实不然,这一篇完全是虚构的。为什么完全虚构的获得成功,以其人真事为基础的没有出线?究其原因,我想就是上面说的道理。
生活是作品之母,这话没错。但是别忘了,还有个“父亲”,即作者。父亲对母亲,不可不亲近,也不可亲近到羁绊和束缚的程度。要有一定的距离,站在较高的视点上去思考、沉淀,溶化。“化”到原来的人物不见了,脑海里浮现出另个更高层次上具有审美价值的人物,方可进入创作。才有可能“优生”。八四年我写过一篇《妈妈也还年轻》,类似的“妈妈”,我熟悉五六十个,她们是被十年动乱荒废了学业的一代,步入中年才有幸进大学深造,其情操、志趣、际遇以至生活方式,同通常意义上的大学生当然有很大区别。要写出来,一人有一段小故事。我很想写她们,但苦于溶化不出一个新的形象。夏天去新疆,回来一人沉闷在漫长的旅途上,想的尽是边疆的风情人物。突然,一个拖着两个孩子的年轻妈妈跳了出来,那五六十个面孔全转幻成她一个人,众多的事情全凝结在她一人身上。
创作上的道理很难一下子说清楚。这篇短文只谈一题,大概也是言不及义之类,只好祈求原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