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叶广芩
“好字!”一位读者指着《西安晚报》文艺版的“终南”刊头说。我看那字,果然质朴挺拔,静穆峻健,终南灵秀,跃然纸上。
书者赵大山,恐怕是位老先生呢。
及至上星期,我才见到了这位“赵老先生”——一个三十出头的小青年。他很忙,求字的,请写条幅的自然不少,他年轻,不能拉架子,有求必应。今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要出他的书法集,日本日中友好书法协会也将为他出版《赵大山日中友好诗谊书法集》,他要准备作品,要拿出象样儿的东西来,这可不是随随便便给谁写俩字儿,抹糨糊贴到墙上的事儿,得认真对待。我看那满桌、满地、满墙的字,心里想,这要花多少时间哪!“你成天泡在字里头,爱人也乐意?”我问。“有什么法子呢?入了这个门儿了。”他说,书法使他着了迷,结婚的那天下午,听贺喜的人说起晚上有几位老书画家在某处聚会,共磋书艺。机不可失,他再不能安心当新郎了,偷偷溜出来,丢下了花朵般的新娘子而投入到一帮老头子们当中。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三点了。
他是他们家最小的一个孩子——老九,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也吃亏最大——没念几天书。有一天他上街,一块牌匾吸引了他的视线,“画片门市部”几个大字苍劲有力,起笔迥峰,气势不凡。他的心颤了,脚也移不动了,瘦小的他坐在马路沿上,托着双颊对那匾看了许久许久,又从身旁拣来根冰棍棒在地上细细临摹,他朴素地体会到书法艺术的魅力,领悟到祖国文字的美感。至于匾额是谁写的,他不知道。后来,他飞快地跑进家门,从家中的各个角落,搜出了自己的全部珍藏,小人书、玻璃球、弹弓以及他最喜爱的一副乒乓球拍……以这些为资本,他从小伙伴手中换了一本“颜真卿字帖”,开始了他的书法生涯。
有失去的,就有得到的。正因为“文化革命”,才纸多、墨多、时间多。亲友来赵家串门,谁都忘不了给他们家的老九捎一捆旧报纸。他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利用这大家资助的旧报纸临帖习字,无分冬夏,十分刻苦,打下了深厚的书法功底。
著名书法家宫葆诚很喜欢这个勤学好问的孩子,给予细心热情的指导。舒同看了他的作品以后,给他讲了一个张旭在唐太宗面前束发挥毫的故事,鼓励他大胆闯新,冲出先人的框子,建立自己的风格。
十几年过去了,他进了工厂,当了工人,后来又调到长安书画社。无论干什么,那笔是一直没有丢。近两年时间,在国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四十余幅书法作品,翻译了近十万字的书法论著,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注意。
七六年,日本书法第一次在西安展出,日本书法那清新的格调、多变的布局使他赞叹不已,同时,一个大胆的设想也在他的心中萌发了:把日本书法的现代美和中国书法的传统美如果有机地揉和在一起,创出一种新的书体,那该多好。于是,他又刻苦学习日语了。
八五年,日本行田市书法代表团来西安进行交流活动,赵大山以他的日本式的淡墨书法和一口流利日语赢得了人们的称赞和好评。
去年,他应日本旭川市梅田书法学校校长梅田雪岭先生邀请赴日进行书法交流,日本著名书法家上条信山先生和关鹭峰先生对他的字都有很好评价,称赞他的书法是“书体变化多端,清静透骨,取东洋艺术之长,溶古今为一炉。”他用彩墨书写的“空海”条幅,作为珍品和中日人民友谊的见证,被市艺术馆收藏。一位市议员,看上了他的一副作品,要出价六万日元购买。遭到展厅管理人员拒绝后,他又私下找到赵大山,苦苦恳求,愿出十万日元价钱收买。赵大山说展品无权出卖,但当看到这位日本人失望离去时,又感到深深的内疚。当晚,他挥毫特意为这位日本朋友另写了一幅。第二天,这位议员捧着赵大山无偿赠送的书法时,惊讶了,“你为什么不愿卖却要送呢?听说中国的书法家并不富有啊!”赵大山回答:“我看重的不是钱,而是友谊。”说完,两个人的眼睛都湿润了。
练习书法,是一辈子的事,活到老,学到老,无止无境。作为西安青年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的赵大山,今后的道路还很长,愿他努力。
(摄影 王幼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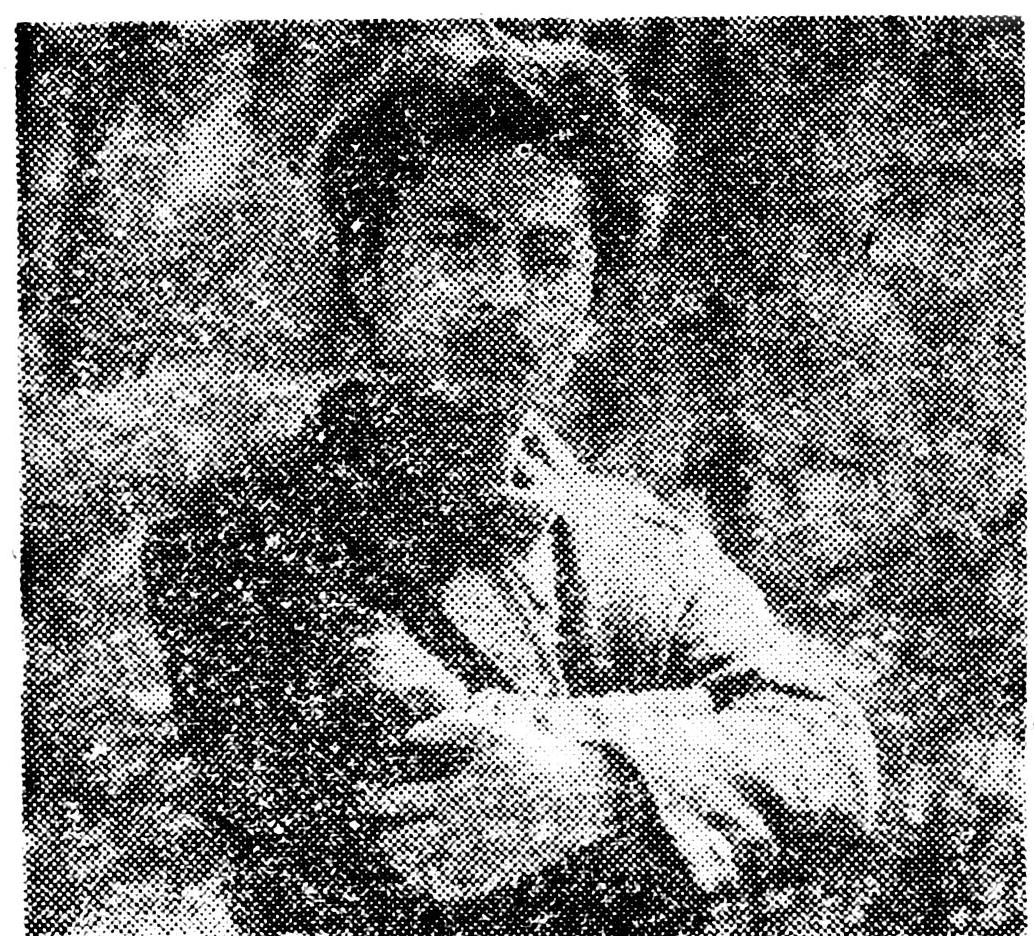
赵大山近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