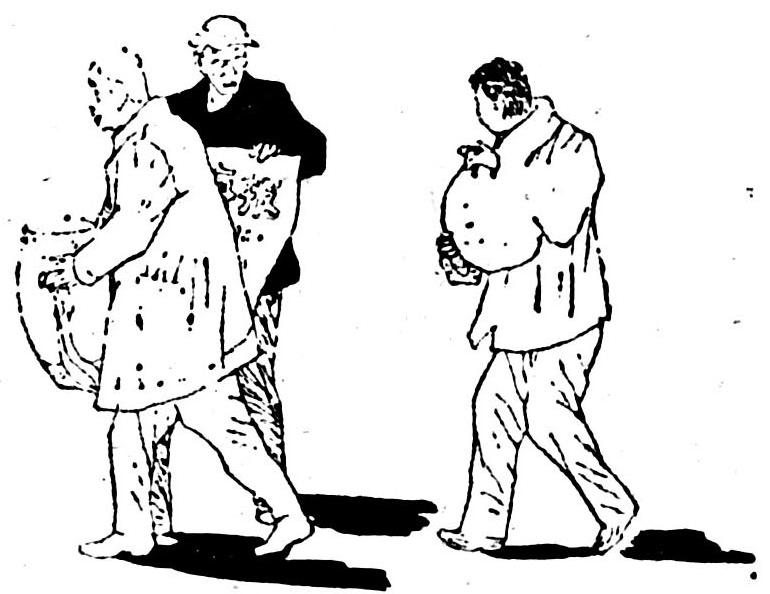谢强
王维耕
西北国棉六厂的露天剧场被数千名观众挤得水泄不通。舞台上,豫剧折子戏《断桥》的帷幕刚刚拉开,台下便爆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许仙”优美的身姿、精彩的唱段、流利的对白,紧扣着观众的心弦。掌声惊动了左邻右舍,将在北边不远处国棉五厂演出的河南开封青年曲剧团的观众拉了一半过来。一折刚完,二折又启。《秦雪梅吊孝》《判姑》……从九点演到十二点,人们仍戏瘾未尽,迟迟不肯离去。
谁能想象到,这是一个厂里的豫剧队的演出!演这场戏的只有四个女演员和一个男演员,而且全是厂里的临时工,平均年龄仅有18岁。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排戏,满打满算不过半个月;又有谁知道,演出用的服装、道具、乐器都是租借来的。还有那三位老人,为了这场演出,贴了几百块钱,跑了两千里路,熬了三十个通宵……
三位是谁?
一国棉六厂卫生所会计谢德生,退休工人张留庆和何并成!
这三位老人从什么时候起嗜上了豫剧无人知晓,但筹备这个豫剧队却有日可查。去年岁末,他们凑到一起说:“纺织城河南人多,咱们弄个豫剧班子吧?”“中!”“中!”各自几十年的夙愿吻合了,一拍即成。
他,现年60岁,今年10月就要退休的谢德生,被封为“队长”。他从小就爱唱戏,京剧!豫剧!河南人爱豫剧,如同秦人好秦腔,退休老人闲暇之余总想听乡音,他就想起了要“弄个豫剧队”。
张留庆,50余岁,退休后在家啥活不干,净拿百十元。可他也有戏瘾,爱豫剧。没事就去找老谢,“想听戏!”相比之下他年轻,就自认副队长,搞后勤。
56岁的何并成,更怪,退休后干起修摩托的营生来。摩托车一辆一辆修好了,看着小青年“扑咯”一声一溜烟骑走,屁股后面还坐着个紧抱腰身的风流女子,他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人得有自己的享受,“组织豫剧队”他只说了个“中”字,就天南海北跑演员去了。
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厂领导和厂工会的支持,得到了俱乐部主任窦敏生的帮助,于是就放开胆子干起来了。三位老人的家成了豫剧队的策划中心,活动中心,饮食服务中心。
跑河南,走山西,找演员。“许仙”就是他们自费到山西晋城“挖”来的。她曾在河南偃师县戏校学了三年,找她可费了不少周折。起初听说她在渭南干临时工,闻讯赶去,母亲已将她领回河南。他们又找到西安她叔父家,得知“许仙”已随一家剧团“游”到山西演出去了。三位老人夜无眠、食无味,常常商量到深夜。“许仙”终于找回来了,他们如获至宝,对她比亲生女还要好。她则以工余刻苦训练作回报,脚磨烂了,膝盖上留下一块块乌紫乌紫的斑痕……
当扮演《吊孝》一折戏中秦雪梅的演员马小玲“扑咯”一声跪在地上嚎啕祭灵时,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位17岁的姑娘竟有如此娴熟的表演技巧,如此丰富的思想感情。她在紧张换装时忘了戴护膝,膝盖骨猛地撞在坚硬的土台子上,钻心地疼哩。
戏演完后,国棉六厂一位70岁的老太婆拉住张留庆家小孩的手:“回去给你爸说,再演几场,我还想看哩。”
老太婆不知道他爸的艰辛,为了不多花一分钱,张留庆不顾炎夏蚊虫叮咬,钻到树林里砍了两根指头粗的树枝做道具(鞭杆),身上被咬了十几个血疙瘩……
要问他们得到了多少报酬,一分也没有。每排演一次戏仅有的五毛钱补助费,三位老人都补助给了演员。全厂数千名职工的热烈掌声,是对他们的最高酬谢。
她们也确实辛苦。上了早班上中班,下了中班倒夜班,每隔四五天才能聚在一起利用休息时间排练几个小时,唯一的收入是按日计酬,上一个班实领工资两块钱。两块钱也就够了,她们找到了所信赖的知音,可以尽情地用自己的演技为众多的老乡消除疲劳带来欢悦,心满意足了。人生得一知已足矣!
呵,几人苦,众人乐。三位老职工组建的这支业余豫剧队,把文明之花送进千家万户,赢得广大职工的爱戴,也为自己的晚年增添了乐趣。
(题图、插图、驰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