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信军 文玫 阿泉
郑高臣不是厂长、企业家。可是在西北国棉二厂,谁个不晓得郑高臣!矮个子,一头长发,见人脖子一缩一缩的,噗哧一笑,一口小白牙……
国棉二厂那么多人,没有谁瞧得起郑高臣。原因很简单,郑高臣蹲过号子。
从劳教队放出之后不久,郑高臣被招进西北国棉二厂细纱车间当工人。除了玩麻将,他没有别的嗜好。业余时间,他这儿倚倚,那儿站站,没个定准。
父亲为了收住他的心,托人说了个媳妇,并急急忙忙娶到家里。那时郑高臣还小,只有二十岁,还不懂得什么叫爱情,稀哩糊涂地结了婚,而他的两个哥哥那阵儿还都没对上象呢。
奇怪的是,有了家,郑高臣依旧感到孤单,业余时间,他依旧感到精神空虚,无聊乏味。一位亲戚建议他不妨搞搞创作,不为别的,就图个精神充实。郑高臣听了亲戚的建议(也只是想试一试),于是就买了几本文学书,开始照葫芦画瓢地划拉起来,倒也写了一些东西,只是拿不出手,老觉得那些个字总冲着自己翻白眼,脸上烧烧的。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终于有一天,郑高臣来了胆量,把他写的一篇以自己的经历为素材的短篇小说拿给《咸阳法制报》去发表。他没见过任何一个编辑,他想象编辑一定很严肃临到上楼时,腿抖了,手抖了,浑身也都抖抖的了。硬着头皮走进编辑室,却见编辑全是笑笑的,这才放下心来,展开稿子让编辑看。编辑看过之后,当时就拍了板:稿子留下,我们发。
腿又抖了,手又抖了。不是害怕,是太激动。
稿子发表之后,郑高臣喊着,跳着,拿给这个看看,念给那个听听,兴奋得一夜没睡着。丈母娘听说女婿发了作品,喜得买了一只大烧鸡犒劳女婿。父亲更是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恰巧他要回河南老家,与自己失散三十多年刚刚找得下落的亲兄弟会面。作为见面礼,他要先把《咸阳法制报》拿给亲兄弟看看,也拿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看看,让他们瞧瞧自己的儿子多有出息——那上面登着俺儿子写的文章呢!
真的,娃子走了正道,全家人都觉着光采。
郑高臣得了拾块钱稿酬,一古脑儿全都请了客,还说那滋味真比他妈的打麻将有味多了.此后,郑高臣一个心眼扑在了写作上。有不吊死在这棵歪脖树上臂不休的气概。当然,他也发了不少。从此,人们对郑高臣便刮目相香了。
然而,郑高臣没有满足。1988年3月,他又牵头搞起了西北国棉二厂文学沙龙。业余时间,他把一帮年青人组织一块,互谈绝妙的构思,朗诵刚就的诗篇:一同去参加文学讲习班,一同去向作家求教。在濛濛春雨中,在飒飒秋风里,他们骑着自行车,奔驰在古都咸阳平展的马路上。带着神往的心情而去,带着兴奋的心情而归,
郑高臣和他的文学沙龙,办起了《晨光》小报,一月一期。没钱,大伙凑,烟戒了,好衣服不穿了,稿费,超产奖,零用钱,有多少拿多少。没有油印场地,就挤在单职宿舍。熬夜,他们不怕。蜡版刻错了,他们重来,手刻疼了,换个人接着干。别人不看,他们自己看。本厂发不出,他们朝外寄。北京、上海也敢投。
不久前那个沙龙会议上,小报的编辑和理事因忍受不了从文的寂寞,提出辞职,这无疑给沙龙带存来了毁灭性的打击。郑高臣一气之下宣告沙龙解散。他踉踉跄跄地来到渭河边,望着东流的滚滚河水,扪心自问;难道就此罢休么,我和他们走到这一步?容易吗?一回头,他猛地瞥见身后熟悉的身影,沙龙成员全都来了,一位理事含着泪说道:“高臣,我们大家议论过了,沙龙无论如何不能散。”象江河喷涌,郑高臣的泪水倾泻而下,只说了一句:“谢谢大家.”
1988年在西安举行的陕纺企业报“七彩潮”征文颁奖大会上,郑高臣作为获奖作者代表发了言。他的坎坷经历和现身说法,博得了与会作家的首肯。对此,省广播电台两位记者还特意采访了他。著名作家路遥给予郑高臣和他的文学沙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你和你的文学沙龙,于写作中提高文化,完善自我。这使我看到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进步!
文学的诱惑力是强大的,她象七色阳光,给郑高臣的心灵以绚丽和温热.

西北国棉二厂文学沙龙的成员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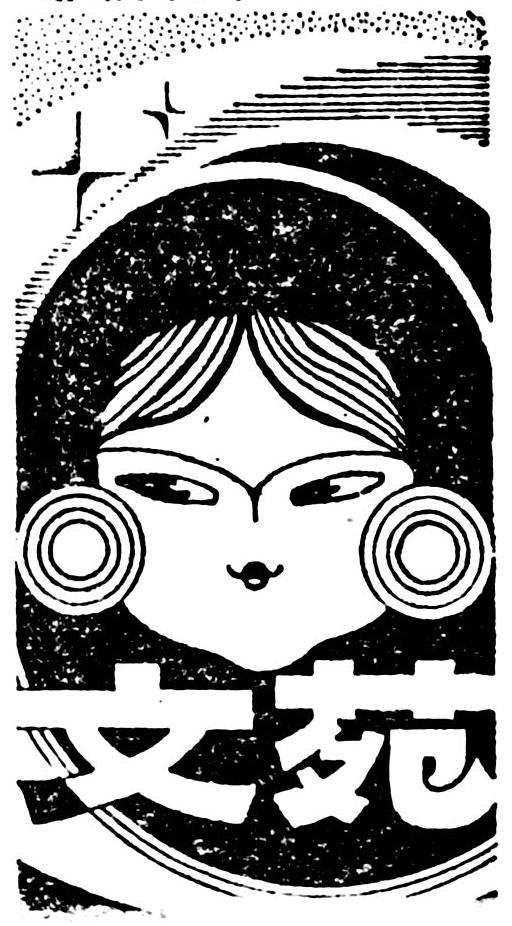
本版编辑叶广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