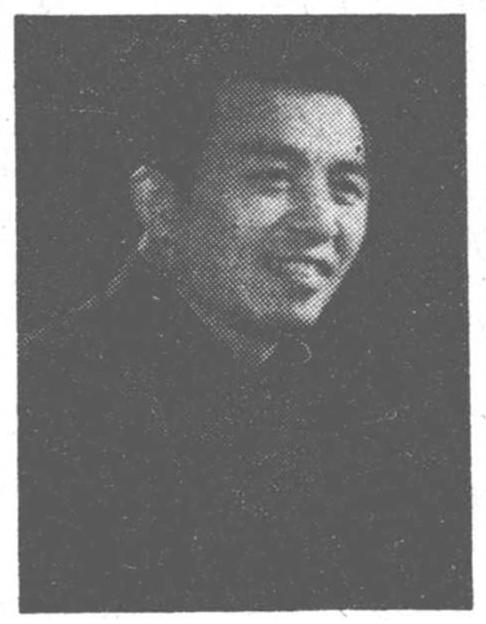李小巴
编者按
三秦大地,人杰地灵。上万个企事业单位育孕出了一大批自己的作家。他们成长于工厂矿山,有着浓厚的生活底蕴;他们生活于广大工人群众中,有着质朴纯厚的气质。今天在这些人中,有的仍身居基层,同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有的虽然已成为专业作家,但其“根”却是扯不断的。无论在何处,他们的名字都为广大职工所熟悉,他们的作品都为广大职工所钟爱。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吟出的那些渗有机油香气,伴着车床轰鸣的诗篇;也不会忘记那些飞溅着滚烫火花,脍炙人口的散文。
“文苑”栏目自本期起,将陆续介绍这些工厂出身或致力于工业题材创作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以沟通作家与读者的联系。
五十年代,我是个探宝者,一名地质勘探队员,“我的足迹遍印祖国西北的
山川大漠”,这不是豪言壮语,这是我青年时代的可贵的经历。
然以文学而言,我大有宝山空回之慨,所著诗文寥寥,实不足论。当然也不乏自珍自爱之作,如五六年的处女作叙事诗《他永远活着》、《柴达木抒情诗》。六〇年后的薄似活页文选的小说集《戈壁红柳》、《正是早晨》,中篇小说《峰巅》等。我珍视我在这些作品中沸扬着的真切和炽热的感情。这些作品和当时的我一样,都还年轻纯朴,无任何矫饰和虚张。
恩格斯当年在谈到法国一些青年政治活动家时说过一句话:“这些人的幸运多于智慧。”我当即联想到我国的文坛状况,近十年来,一些中青年作家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我这个半老头子自然难得幸运,也少智慧,倒是个十足的愚者。六四年我调到作协搞专业创作后,并未“专业”几天;六四到六五年去陕南搞了一年社教;接着就是十年动乱。我倒象个拓荒者,地质、石油、煤矿、冶金、纺织等等,都留下过我镢头的痕迹,好多田块来不及播种收割就又撂荒了。我自己也感到对不住我的汗水。六五年下半年,我到铜川煤矿深入生活,当了近乎半年的井下工人,那是很认真的。我曾在残采区队里跟了半个月班,在不到一米高的掌子面中爬着拉小车,唯一和《燎原》中不同的是,我头上顶的不是鸡儿灯,而是明亮的矿灯。只可惜,我当时除了写了一篇《矿长的星期天》外,长篇还来不及写,就被十年动乱搞的搁了浅。如今我正步入老年,这段生活就很难接续了。想来令人痛哉!当然我也有歪打正着的时候,七四、七五年,我到陕北和北京知识青年厮混了一年多,这方面的小说没写出,倒写出了一部《啊:故土》。我相信我的这部作品的生命力。
这多年,我的精力和兴趣转向了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文学理论研究方面,时时有论文写出、刊出。事情往往是这样:越是结识世界文学巨人多,就越感到文学之精深是个什么样子,是怎么个难法。因而也就不想去经营那些轻浅、粗浮的平庸之作;然而创作精美之作品又谈何容易?我常常感到我就象是个自不量力的登山者,偏要拣一处陡峭的岩壁向上攀援,也许最终会坠入深渊。但我不悔。我崇尚牺牲了的勇者。
“抱瓮灌秋蔬”,在古人看来即愚也,迂也,何况时人?想来想去,我多少与这位汉阴老翁相象,故而我不觉得他有什么好笑。还是那句老话:人各有志。文学亦然。
李小巴,五十三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书记处书记。山东郓城人,生长于黑龙江省。人生三大阶段:学生——地质队员——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