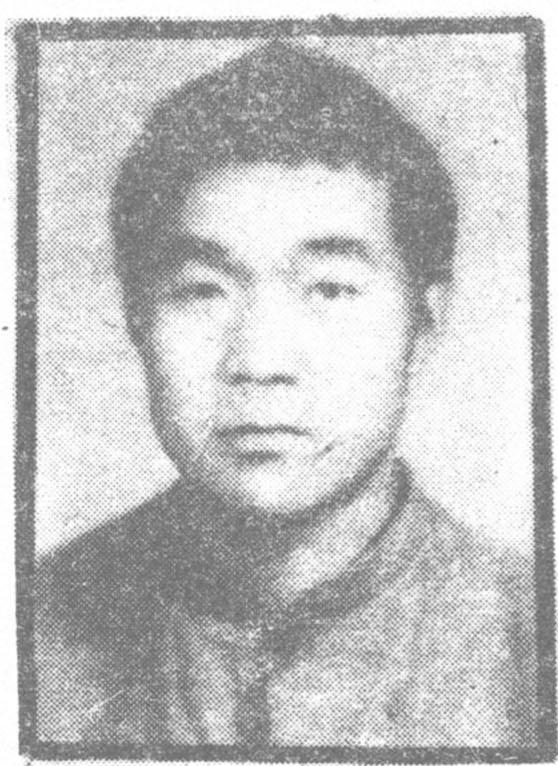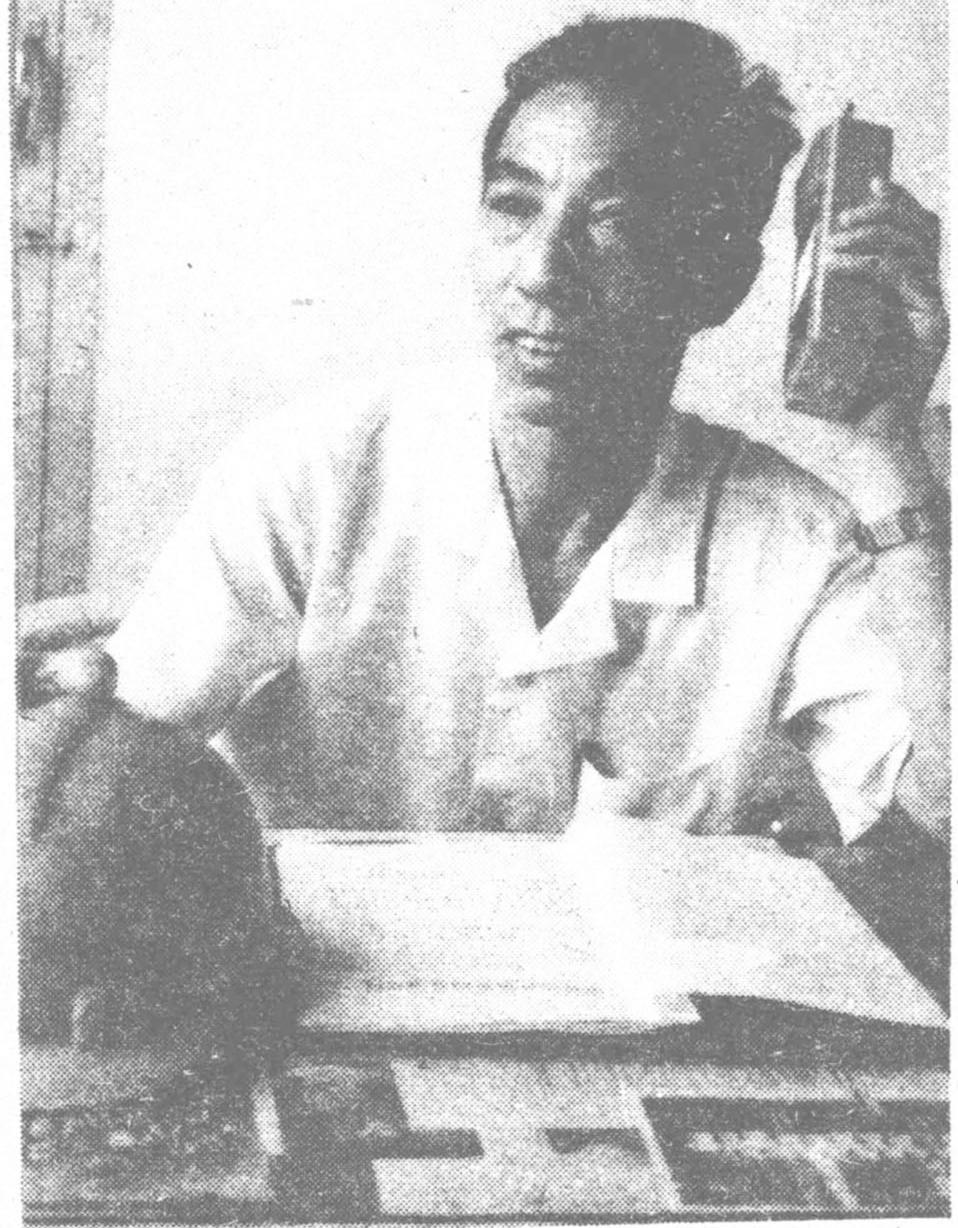一辆陕西省化工安装工程公司的救护车,驶出古城西安,辗着深秋的霜露,沿“西包”公路持重而平稳地北上。
霍天雄在担架上,身体看上去依然很魁梧,只是那张原本方正、黝黑的脸,被病魔折磨得浮肿、发黄、憔悴。15岁的女儿偎在他身边,眼睛哭得桃红。她知道她爸爸正在向另一个世界走去……。
汽车在蜿蜒起伏的陕北高原上小心翼翼地行进着。
交口河畔那座陕西省最大的炼油厂延安炼油厂已依稀可见,隆隆的机器声亦隐约可闻。霍天雄支撑着坐起身子,爬在车窗上寻梦似地张望着。1987年,他随化安公司工程队来这里施工,三年的常规工期,一年零八个月完成,创造了陕西石油化工安装史上的奇迹。“延炼”人和干“延炼”工程的人,都忘不了那个粗犷、豪放、质朴得象黄土地一样的陕北汉子,那个集豪爽与憨厚于一身的电工班长。
七月流火,气温高达40度。露天施工,加之铁板、设备的烘烤,连“知了”都热地喊哑了嗓子。被人们公认为“铁人铁嘴豆腐心”的霍天雄,突然在施工现场大光其火,只见他又粗又红的脖梗上青筋高暴,叫老子骂娘地拦住别人,自己一个人爬上滚烫的蒸汽管道……结果,绝缘鞋的胶底被烤化了,脚心烙起了一个又一个红枣般的大血泡。他不在乎,反倒盘膝席地而坐,边挑泡边风趣地说:“嘿嘿,老子倒要看看,是你烫得快,还是我老霍挑得快!”
霍天雄家居陕北农村,上有80岁高龄的奶奶,下有尚未成年的儿女,可参加工作20年来,这“一头沉”的日子全靠体弱多病的妻子一肩担,而他的兵,谁家住农村,谁家子女多,谁正恋爱,他都了如指掌,尽量予以照顾。他当电工班长14年来,替同志们顶班干活的次数谁也记不清了。只清楚地记得,他从未因此而多拿过一分钱的奖金。从1983年到1989年,他连续5年主动放弃了探亲假,从参加工作至今,竟无一次彻底帮妻子收割完一季庄稼。妻子曾多次抱怨他说:“你是公家的人,我们家住店的客。”他听后习惯地一犟脖梗,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吃国家的粮,拿国家的钱,要把国家的事儿抛一边,回家干私活儿,心里总觉得不对味。”每次,他总是这样实实在在地要求自己,实实在在地安慰妻子。
在“延炼”,霍天雄靠精湛的技艺和赤诚的事业心,赢得了厂里的信任,厂方以解决家属户口和儿子工作为条件,聘用他,这对他来说真是喜从天降。他忙将此事信告妻子。眼看夏收将临,妻子三番五次来信。一面催他尽快调转,免得夜长梦多,一面催他回家夏收。此时,“延炼”,工程正值施工高潮,闻知此事的公司领导找他谈了一次话:“天雄呀,化安公司需要你,可不同于新建厂矿,无法为你解决家属户口和孩子工作问题,这……”看到领导内疚而又焦虑的样子,他什么话也没说,就死心塌地地留了下来,甚至夏收连家都没有回。
1988年7月的一天,正当他汗流夹背在现场干活时,他那年满16岁的独生儿子不幸堕崖身亡。噩耗传来,这位从未掉过一滴泪的铁汉子,瘫倒在地,失声痛哭起来。领导和同志们流着泪打发他回家,同时,又为节骨眼上的工程担忧。此时,工期延误一天,就要给国家损失人民币10万元。正当大家忧心如焚的时候,霍天雄匆匆料理完儿子的丧事,拖着疲惫的身子赶回工地。他红肿着眼,操起工具,就投人了紧张的施工,感动得在场的人个个潸然泪下……。
车子到了陕北永坪镇,瞧着徐徐从眼前掠过的永坪炼油厂,霍天雄的心里油然生出浓浓的歉意。因为,这是他一生中唯一没有干完的工程……
今年春天,与丹江岸边的春燕一起飞跃过秦岭的霍天雄,来不及洗刷从商县冶炼厂归来的征尘,又匆匆来到了这曾经养育了他的故土施工。这时,他就觉得腹中不舒服,时有疼感。可他身体壮实,大凡素日的小灾小病,挺挺身子就过去了。然而这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工期与病情均越来越吃紧,有时痛得他脸色蜡黄,不得不蹲着或抱着肚子干活。实在挺不住了,就抓几片止痛药塞进嘴里。同志们见状,着急地劝他去看病,可他脖子一犟说:“看啥病,离你们送花圈的日子还远着啦,快干活!”他原打算加把劲儿,9月底完工后,再看病。他毕竟是血肉之躯呀!此时,可恶的病魔正向他躯体深处悄悄地侵袭。在永坪,这位硬汉子的病体实在支撑不住了,终于被同志们送进了绥德医院。经初步诊断,为“晚期肝癌”!
公司领导得知他的病情后,立即派人将他送住西安,不惜一切代价诊治。当他知道自己的病情后,一再向前去探望的领导和同志们提出:公司资金紧张,不要再花钱了。后来,公司领导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低头想了半天说:“我想回陕北老家去好好陪一次奶奶、大(父亲)、娘、老婆,还有死去的儿子……。”
在家乡苗家坪,当霍天雄扶着车帮走下车时,暮秋的黄土高坡静得瘆人,人群里一声饮泣一时竟连缀成一片呜咽。天雄无力地微笑着和乡亲们打招呼。这时,人群呼啦闪开一条道儿,父亲来了,母亲来了,妻子来了,八十二岁高龄的奶奶也来了
霍天雄转进子洲医院第二天,即10月2日,他给护理自己的家属整整发了一夜脾气:“明知是不治之症,非要来医院白花钱,不花自己的钱心不疼?……回!明天一定回家去!”10月3日,他回到了生育他的苗家坪。这天正好是中秋节,家里为他包了饺子,他已一口也不能下咽了,就让妻子给儿子坟上送了一碗,然后,自己静静地躺在炕上,默默念叨着谁也听不清的话语,陪全家人渡过了参加工作二十年来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团圆节……
本报通讯员 商琼 冯梅
本报记者 柳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