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焕龙 魏波
在当代文学史上,崔八娃曾是名播中外的“战士作家”。五十年代,他与高玉宝齐名,在中国文坛上刮起了“西崔北高”的劲风,受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当选为参加“五·一”观礼和全国青代会的作家代表。他的《狗又咬起来了》等自传体小说,被译成多国文字,并选入中小学课本,使用了三十多年。奇怪的是,这位红极一时的知名作家,只搞了四年创作便自动休笔。如今,他已退休还乡,在陕西省安康市沈坝乡沙沟村过着与山为伍、与土为伴的农人生活。崔八娃究竟缘何创作、怎样成名、为何更名、并在弃文务农后是怎样生活的呢?本文将告诉诸位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
崔八娃的出现
沙沟中部,有一条小沟。沟垴上,绿山环抱,水田平铺,人称此地为“躺椅”。崔八娃的家,就住在“椅座”的正中。因为父辈三兄弟共养了十个男孩,他排行老八,便得名“八娃”。
1949年农历3月13日,抓壮丁的保丁把他抓到了乡公所,那年他刚好20岁。
他被抓到平利县,才跑了上十天,连枪都没摸过,就因平利解放而投诚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随部队参加了解放安康、西乡和青海剿匪等战斗。1951年,部队转移到陕西凤翔县,一边支援地方土改,一边开展扫盲运动。
当时,部队推行“速成识字法”,就是在汉字旁注上拼音,学会拼音后,再硬背汉字,一共两千三百个单字,要求十三天学完。放牛娃出身的崔八娃,深知没文化的苦处和学文化的益处,他不分黑明地苦背苦记,提前两天完成任务,被连上评为“扫盲标兵”。为了巩固学习成果,部队要求每个士兵从写信、记事入手,每天练写一篇作文,还对好作文逐级上报,给予讲评、发表等奖励。
这年秋天,刚刚摘掉文盲帽子的东北军区战士高玉宝,发表了成名作《半夜鸡叫》,一时轰动全军,成为学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并在全军将士中激起一朵银光四射的浪花。
崔八娃所在连队的文化教员张家先,是个高中毕业生,家住石泉县农村,读了《半夜鸡叫》之后很受启发。他认为本连大多数战士来自农村,与高玉宝有着相似的经历,也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他认真讲解了几遍《半夜鸡叫》,并仿照这个路子出了两道作文题,以作业的形式要求战士们完成。
崔八娃选择了其中的《狗又咬起来了》。
他写了大半夜,回忆着家乡的真人真事,把恶狗咬穷人的事一个个写了出来,写了十几件,只有三百多字。第二天清早,他就高高兴兴地交了上去。但到上课发作业时,唯独没有他的。下课后,教员才把作业给他,只见上面批了六个字:“没写好,要重写!”
他又改了大半夜,写了四百多字,满以为可以了,但教员又批了十个字:“写事要集中,再删几件事”。
第三遍写了四件事,每件只写两三句话就没词了,连同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在内,还不到两百字。这回教员没有批字,但下了一道死命令:“啥时把它写好,啥时再写新的。”
一连十几天,别的战士都写了十几篇新作文,崔八娃还在“原地踏步踏”。
又过了十天,崔八娃把第五十稿交上去,教员满意地笑了。他把这篇只写三件事情,篇幅上千字的作文逐字逐句地看了又看,最后改了几个错别字,又叫崔八娃重抄一遍,连同另一篇作文,一起报到师政治部文化科。
第九天,文化科科长把崔八娃找去,让他进一步修改。崔八娃望望科长,又看看手中的作文,不知从何改起,也不知自已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改了一个来月还不放过。柳科长看出了他的心思,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能写出这个程度,很不容易,不要轻意放弃。这跟做饭一样,抓火候的时候加一把火就熟了,少一把火就坏了。”
崔八娃又改了三天,认认真真地写了两件事,文字也通顺了些。
第四天,科长找来一个中年人帮他修改。这人名叫段新华,原是国民党部队的连级干部,起义过来之后就在文工团搞写作。段新华看过崔八娃的稿子,对他说:“一篇文章最好只写一件事,写深写透就行了。”他指着搞子进一步开导:“保长催米这件事就好,很有故事,你就把这件事系统回忆一下,用功去写。”这下,崔八娃豁然开窍。恶狗怎样疯咬,保长怎样凶狠,父亲怎样被打,母亲怎样奔波……往事历历在目,件件牵肠挂肚。他再不照稿改稿了,把原稿丢下,另起炉灶,一夜时间,就写成了自传体小说《狗又咬起来了》。只是,那时他不懂文学,科长和教员也不知道这就叫小说。
段新华帮崔八娃改了两遍,柳科长又召集科里的几个笔杆子“会诊”了一次,大家认为可以了,就决定上报。然而,报向何方?众人议了一阵,觉得《半夜鸡叫》是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的,不妨也去试试。于是,他们便以“上报”的形式,把稿子投到了《解放军报》。
1953年元月,《狗又咬起来了》公开发表了。
崔八娃走红
建国之初,部队文化生活相当寂寞,能写信、会念报就成了“秀才”。一个刚刚脱盲的士兵,竟然在军报上发表了小说,其轰动效应很快波及全军乃至全国。
一时,各大报刊上,迅速掀起了“崔八娃热”。《昔日放牛娃,如今写小说》、《扫盲出奇效》、《战士崔八娃,创作结硕果》等通讯报道相继出现。一些著名作家也纷纷提笔,为《狗又咬起来了》发评论,唱赞歌,有评故事情节的,有评人物描写的,有评主题思想的,有评语言特色的,也有评手法优劣的。这些评论,把崔八娃看痴了,他压根没有想到:自己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水平?他又在寻思:自己老老实实写的山野杂事,经名人一评,怎么也和大作家的大作品一样神乎其神了?
当月,西北军区授予他“学文化模范”光荣称号,并给他记了三等功。拿到大红喜报和闪光的勋章,崔八娃急了,他问文化教员:“这可咋办?”教员平静地说:“你好好学,坚持写就是了。”然而,没过几天,更大的新闻令他震惊:报上刊出一条决定,号召全军战士向他学习。崔八娃更急了,急得寝食不宁。
不到一个月,上级来令,调他到兰州从事文学创作。临行前,柳科长拉着他的手,反复叮咛:“多写你熟悉的事,好好写。”
记着这句话,他一到西北军区文化部文艺科就埋头写作,每写一篇就按当时的制度,交给科里,由大家评议,然后反复修改,大家都觉得比较理想了,就投往《解放军报》。
这年春天,是崔八娃一生最明媚的春天,他的自传体小说《一把酒壶》、《卖子还帐》、《郭大肚子》等相继在《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并被其它报刊转载。
这年春天,他的作品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了国外。
这年春天,他和“战士作家”高玉宝一起,在中国文坛上刮起了“西崔北高”的劲风。
这年春天,他由一个放牛娃,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53年4月底,部队接到通知:速送崔八娃赴京参加“五·一”观礼!
崔八娃首次来到日思暮想的首都北京,首次见到了万分崇敬的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五·一”之夜,北京城里人海欢腾,崔八娃却无心观赏。他趴在招待所的书桌上,一气写成散文《见到毛主席》。第二天天不亮,他就去找邮局,小心翼翼地将稿子投进了邮筒。没过几天,这篇稿子又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
会后,首长不让他走,通知他到怀仁堂参加团中央召开的“五·四”座谈会。这次人少了,他见到了高玉宝。二人相见如故,叙谈了大半夜,最后互问:“今后咋办?”谁也答不上来,互相鼓励一番,便茫然地分手了。
回到兰州,他一时写不出东西了。虽然当时每天都有十几封约稿信,虽然当时他每天笔不离手,但思路很乱,熟悉的写完了,不熟悉的写不成,他时时在想:我算完了!
这年十月,他再次进京,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竟和著名作家郭沫若、巴金、茅盾、丁玲等人同室议事。他又问高玉宝:“今后咋办?”高玉宝还是摇头。
10月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与会代表,他和高玉宝有意站到后排。没想到,正好站在毛泽东的正后方。照片在报上刊出时,两边的取了,留下中间部分,这下他的名声更大了,人们说:“毛主席只接见了百十个人,就有崔八娃,真了不起!”
那年月,毛泽东是神,受他接见,如同受神洗礼,被接见者顿时身价倍增。一个月后,照片从北京寄来,长达一米,好几百人,崔八娃只露出半个头。但就这样小心谨慎的一次露面,也被部队官兵视为“无尚荣光,无限幸福”,很是风光地宣传了一阵。
一天晚上,崔八娃蓦然冒出一个想法:当初我写的是《狗又咬起来了》,现在简直成了“人又吹起来了”。老实巴交的崔八娃想把这种心境写出来,想了几天,也没找到合适的表现手法,就不再管别人咋宣传了。
这时,有几名“战士作家”相继进大学深造,好心人劝他申请学习,他向首长提出了要求。首长权衡利弊,为了保住这棵苗子,并能不间断地争光,就让他就近在兰州上部队办的速成中学,一边学习,一边创作。两年学习期间,他只创作了两篇作品,一篇反映探亲前的思想冲突,取名为《上车之前》;一篇取材于儿童生活,取名为《岩生》,《岩生》的发表,为他的创作生涯划上了句号。
速成中学毕业后,他又回到了陕西,在长安县兵役局工作。这下,三秦大地再次掀起“崔八娃热”,陕西人民出版社将其二十余篇作品全部收齐,出版了一部名为《卖子还帐》的小册子。各种报告会邀请书雪片样飞来,政工科成了安排崔八娃作报告的“接待站”,收发室几乎成了崔八娃的服务班子,每天来信不下十封,有约稿的,有谈心的,有读后感,也有决心书。他实在无法一一作答,就按领导意图,写了封公开信,寄到《人民日报》。歪打正着,这封信真被公开发表了。于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崔八娃更神了。有人说:“连他的信都能上全国首位大报,可见此人实非一般!”
军营的墙外,贴着反对封建迷信的大幅标语;军营的院内,崔八娃被看成了非人非神的天才。
更名“崔云风”
1958年6月,崔八娃退伍还乡,他把一担过百斤重的书籍朝楼上一放,就操起锄头参加集体劳动。这年7月,家乡刮起“吃食堂风”,大部分人都饿得无法下地,公社领导见他当过兵,体质好,能出力,就让他担任大队长。
他本想带领群众开荒种地,填饱肚子,但又一阵风吹来,要大搞社教运动,他被抽去一连搞了三期。
这天,他到公社参加社教工作经验交流会议,路过学校时,听到学生们正在高声朗读他的作品,他就停下脚步。下课了,不少认识他的师生都来和他打招呼,但这些人却不知道:眼前的崔八娃,就是写书的崔八娃。
刹那间,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更名。
取个什么名字呢?他想了几个月,也没想出来。
1959年秋季,上级决定,调他到信用社当主任。信用社主任,掌管财经大权,需要一枚印章。刻章之前,他想了一夜,想出了“崔云风”三个字。
“崔”字为姓,按他家的排行应为“道”,为何取名“云风”?一直是个谜团。
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他才向笔者透露:
“当初,父母没有给我取名,我也取不了名字,就只有小名没有大名。后来,我能给自己取名了,也到了正名的时候了,就应该好好给自己取个名字。‘云风’这个名字,有三层含义:一层意思为提醒自己,我曾经被一阵风吹了起来,架到了云空,再想真真实实地做人,就得风吹云散,看清自己;另一层意思表示弃文务农,退到云遮雾绕的山乡,就不再出风头,安安宁宁地工作和生活,做个隐居之人;第三层意思有政治含义,当时社会上风起云涌,自己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不高,要站稳脚跟,就得加强学习,催散风云,看清形势。”
然而,人们不管他是咋想的。在那个年代,几乎就不存在个人意志。
或许那时“登险峰”、“攀高峰”比较时髦,公社领导让他改为“崔云峰”,他不改,人家就在任命文件和干部花名册、劳动出勤表上写成“崔云峰”。
次年秋季,地县领导得知大作家崔八娃如今就在本地供职,而且干着与身份极不相称的工作,就一张调令,把他推上了《安康日报》社的编辑岗位。
听说崔八娃就在本地报社工作,人们又开始起哄,希望拜读大作家的新作品。报社领导清楚:老崔文化素质太差,又没学过新闻,连编稿都很困难,然而,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只好安排他试作一次采访。
按照领导提供的线索,崔八娃来到安康军分区养猪场,采访了一下午,折腾了大半夜,写了一篇不足三百字的消息。发表时,署名“崔云风”,读者不知何许人也,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实在做不了编采工作,报社就安排他当保管员,继而到农场开荒种地。
1962年,正值自然灾害盛年,中央发出通知:凡属1958年后从农村参加工作的都属精减对象,动员其回乡支援农业生产。
崔八娃再次审视“云风”二字,又把思路返回到当初更名的动意上来。他再也坐不住了,主动辞职,回乡务农。
一年后,他担任了大队长。
三年后,他担任了信用社主任。
直到1980年退休,当地人除了当面喊“崔主任”,背后喊“崔八娃”之外,根本不知道他的曾用名、也是他真正的学名——崔云风。
只是每天早晚,他在默默地给自己点名时,无声地喊着:“崔——云——风!”
崔八娃揭谜
近年来,崔八娃再次被人们抬出来,主要缘于两次来人来函:
1984年,《当代作家辞典》编辑部为编写“崔八娃”辞条,发信向他本人索稿。信寄到兰州军区,被转到陕西省军区,又批到安康军分区……历时数月,查无此人,因惊动面大,再次扩大了崔八娃的影响。一时间,到处都在寻找崔八娃。最后,由安康市委宣传部出面,才找到了崔八娃本人。
第二次是1989年,崔八娃原所在部队——兰州军区某师政治部副主任杨大勋等人,因代表部队参加“解放安康四十周年大庆”活动,听到了有关崔八娃的故事。这位三十来岁的军官怀着好奇心要去拜访崔八娃,市上就派车把他送了去。谁知,这事竟被人们传为:崔八娃又要走红了,兰州军区派人看他了!于是,在有关“虎老雄风在”、“东山再起”等议论中,把他变成了新闻人物。
事实上,今年63岁的崔八娃,依然耳聪目明,思路敏捷,身体健康。劳动上,他担大粪,抬石头,和小伙子不差上下;生活上,他衣着朴素,饮食正常,常年很少生病;政治上,他既关心国家大事,又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是远近有名的“文明之家”。
当我们结束采访,临别时,他拉着我们的手,一字一板地说:
“人民养育了我们,我们要对得起人民!”
(题图 裴广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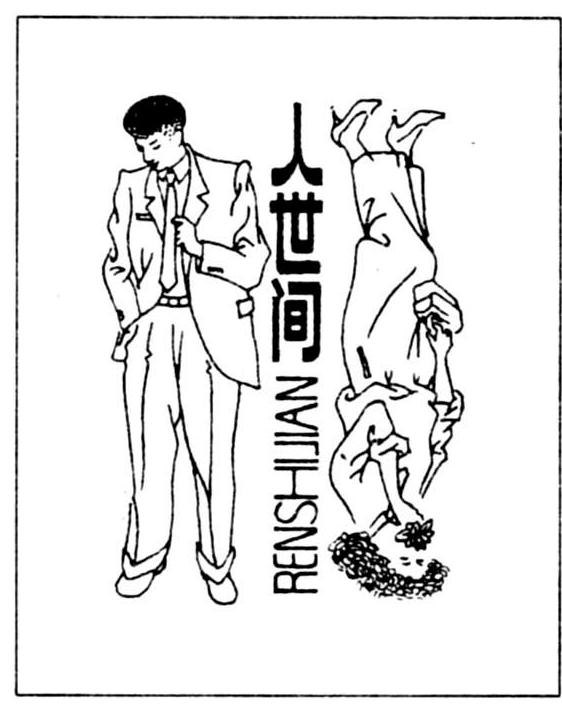
刊头设计郑志
本版编辑 周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