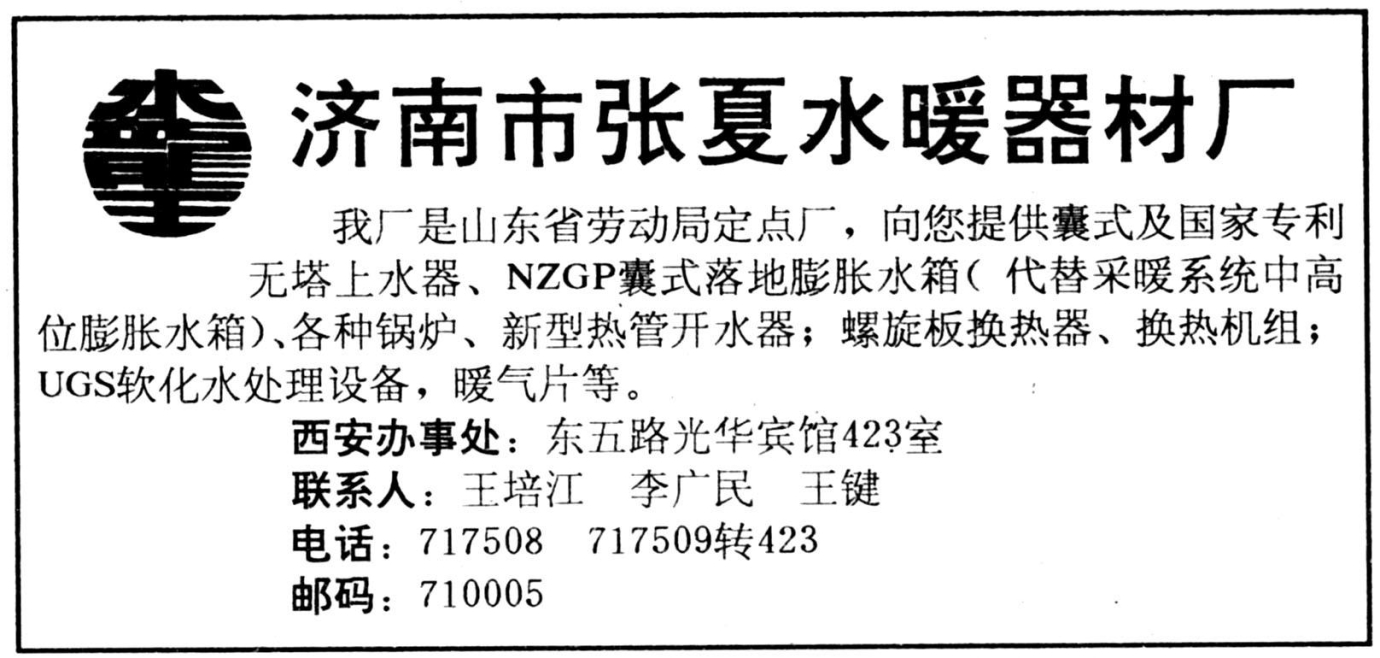据本报9月30日《陕北煤气田浪费纪实》一文所提供的资料表明,我国能源总耗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能源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国大约缺煤2000亿吨,缺油1000亿吨,缺电5000亿度。约有20—30%的生产能力因能源短缺不能发挥作用。
然而我国对于能源的浪费却是惊人的。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消耗每吨标准煤所创造的价值为469美元,印度是1265美元,日本是2825美元……
一方面能源紧缺,一方面能源浪费,这就是我国目前在能源问题上的两大困惑。
但这同时更说明,我国在节约能源方面大有潜力可挖。胡睿,一个52岁的普通女工程师,就是带着这样的使命,1983年在西安仪表厂挂起了节能办公室的牌子。9年来,她克服重重困难,白手起家,从管理入手,对厂内耗能设备进行了50余项技术改造,节煤4000多吨,节电320余万度,节资达560多万元。使企业在产值比原来翻了三番的情况下,能源费用却有所下降。1987年西仪厂进入国家二级企业,1990年全省第一个跃入国家一级企业预备期。胡睿自己也先后13次被评为省级以上先进,并被机电部聘为国家级企业节能考评员。
胡睿,一个女中强者。
1973年,根据机械厅指示,西仪厂决定建立节能机构。然而数千人的大厂,竟然找不到愿意干的人。厂领导说,哪怕找个闲人,让上面知道有这么个机构就行。领导找到当时在动力分厂担任电工的胡睿。
“槽里没有马,拿驴去支差。你又不懂那一行,去能源办不是往坑里跳吗?”
同事都在劝她。的确,当时的能源办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地方没地方,领导又不重视,其他分厂怕限制他们的能源供应,更不支持,简直是光杆司令唱空城计。果然,胡睿上任不久,上级节能验收不及格。为了使工作有些起色,胡睿求厂里拨千把元买台充电器,也没有着落。她的心凉了,同事的话又在耳边回响。但是凭着她对工作的责任心和永不服输的性格,她憋着一口气,查阅资料,请教专家,自己设计,自己组装了一台充电器,效果不错,她又装了8台,无代价地分送到几个分厂,从而换得分厂对她工作的支持,终于顺利地安装了200多台能源计量仪表。当年就为厂里节约了40多万元,也使厂领导对能源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在胡睿的据理力争下,厂里终于给她配备了新人,健全了机构,建立了三级节能网络。胡睿趁热打铁,立即着手对全厂800多台耗能设备及站房转换设备进行了效率测试。建立监测点592个,能源计量表配备率达到95%,监测率98.5%,并逐步对其进行了40余项有突破性的技术改造。使全厂年节能资金达到70多万元,能源消耗稳步下降。1985年西仪厂被省机电厅评为节能先进企业,并获国家计量二级合格证书。1986到1988年连续三年被评为节能二级企业。1989年被评为节能一级企业。次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一级企业预备期。
“胡睿不简单呐,她是我们厂无冕之厂长。”这是厂领导对她的评价。事实上,在技术方面,她对全厂的了解远比任何一个厂长都要详尽。每个分厂每个车间乃至每台车床的构造性能,耗能情况她都了如指掌。所以有关业务方面的厂长会议,胡睿都被破格吸收进去。她何止在厂里受宠,就是全省节能知识竞赛、能源成果展览等活动,都是以胡睿主管的西仪厂能源办作为阵地的,她的水平就是陕西的水平。
熟悉胡睿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她不象是个女人,倒象是个顶天立地的硬汉子。
1986年是她从事能源工作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两个月内要对全厂800多台设备进行检测,同时还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厂里虽然给她增加了新人,但都是新手,每天的工作都得她指导着干。甚至她上厕所时,也被人半路拦住:“紧不紧,不紧就先跟我看看去。”
更不幸的是,那时她的丈夫因心脏病住院,家里还有偏瘫的母亲和80多岁的公公需要照顾。两个孩子一个很小,一个正在参加高考。厂里、医院、家里一样也离不开她。她不是孙悟空,没有分身术,但她却要干出三个孙悟空要干的事情。每天在这三点之间不知要跑多少路,她挺住了。直到上级验收的那天凌晨两点多,她在丈夫的病床边将数万个测试数据和图表汇集成册,才抓着丈夫的手睡着了,这一觉睡了两天两夜。
本报记者 惠焕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