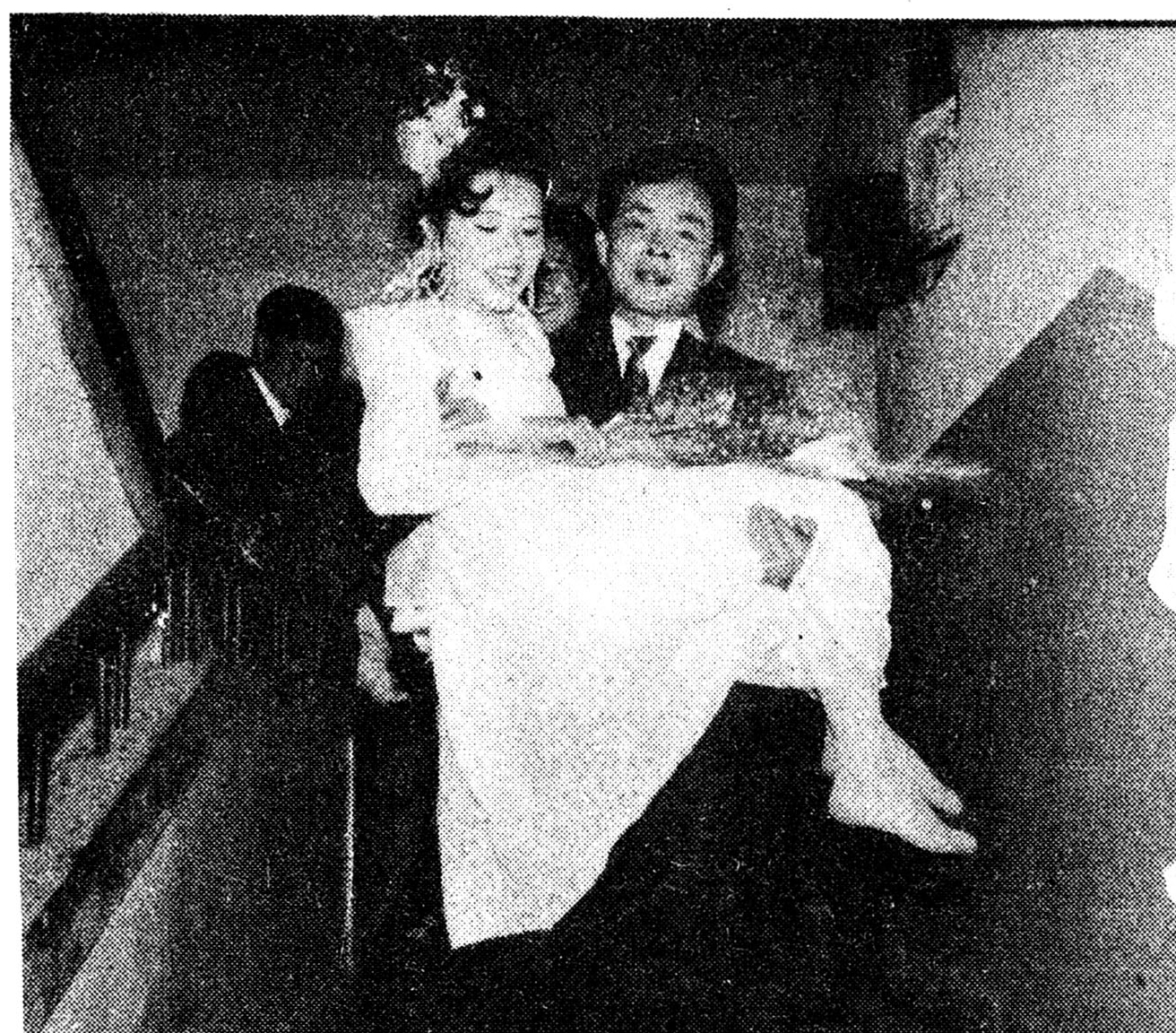(西安) 田原
见过一幅人人说好的漫画:处长向楼上搬煤。一年轻人讨好地前来帮忙,忽听女邻居耳语说处长已退休,年轻人立马不辞而别,只剩下退休的处长纳闷不已。漫画好就好在活画出势利之人的精明,帮忙的对象讨好的对象是“处长”或者说是处长手中的权力而决不是处长本人,人与权一旦分离自然是“人走茶凉”。善良人看过自然会心头一快,受此冷落者看过,或许也会轻舒一口郁闷之气。
人们虽然都鄙视势利者。但是势利自古以来就是社会心理的顽症,是人性中的劣质,经过人类社会世代的积淀,也和人类社会的种种美德共生共长,决不因讽刺嘲谑而绝迹。
战国时苏秦挂六国相印,威风凛凛地回归故里,原先看他不起的老父、长嫂转眼间变得恭敬谦卑起来,让苏秦大发“何必前倨而后恭若也”的浩叹。前倨微而后谦恭无非是因为苏秦已变恭发迹,当然“苏秦还是旧苏秦”。这种势利者的热脸和冷眼油然作云,沛然行雨,千百年来常在人面前晃荡。这一类因人的境遇变迁迅速变化的面孔和心理,就是“势利相”和“势利心”,变化的最终依据是“势”,是“利”,是权位是利益。
当然历史上也有不势利的,有人格自尊的。譬如介子推。他与重耳周游列国,断粮时“割股伺君”,重耳后来为晋国国君又成诸候霸主,但“介子推不言禄,禄亦不及介子推”。介子推大概是羞于启齿觉得计较起来没有意思,就隐居起来,逼得重耳放火烧山,结果介子推抱树而死,最终还是“不言禄”,后世的人们纪念他的骨鲠之气将他的忌日定为“寒食”节。张良也不势利。他扶佐刘邦得天下,刘邦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但子房(张良)终究不愿封候拜相却随黄石公而去,功成不居让千载以下的贤人智者倾慕。严子陵也不势利。当年与微贱时的汉光武帝成知交,待汉光武成了皇帝,请他出来,严子陵最后还是到富春江边去钩鱼,决不为官。世事滔滔,势利的尽管势利,自尊的却照样自尊。征之史书,劣质与美德辉映,浊行与清流并生,源远流长,余波激荡。至于多少人经历过势利的挤兑倾轧,受过势利的冷暖寒热,遭过势利的损益,那不用算计,也算计不出。即使愚陋如我的乡亲,也慨叹: “穷在街头无人问,富有深山有远亲”,似乎是给势利这种世风一个真切的注脚。
从古到今,势利似乎带上某种普遍性。何以如此?答案不尽相同。古代名将廉颇兴旺发达时,宾客如云门庭若市,失势时,树倒散猢狲门可罗雀,明智经验如廉颇老将也想不通,一位智者解释道: “夫天下以市逆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 “市道”者商品交换之道也。附势是为了趋利,失势则无利可趋,本是常理常情,不必大惊小怪。这现象虽不敢说是天下人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起码言中一部分世道一部分人心。鲁迅先生也为此发过怵心之论,直指人情世态中的劣迹:“……少单身鏖战的英雄,少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云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这不刊之论透露出之所以势利若此,是因为切身的利害,至于是非之类是根本不讲也无须乎去讲的。
势利的原因说到底是人的现实利益的得与失,也算是物质决定精神吧。在精神范畴,势利是人与人关系的一种概括,属于道德评价。道德期于人的行为理想而又规范,但现实利益又来得那样实际而又真切。这便矛盾便斗争,便产生“势利小人”、 “趋炎附势”的道德责难与警策,便产生“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风范的礼赞与呼唤。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世风世道人情人心趋利避害的本能与道德义务的践行,永远会处于一种矛盾搏击之中,在个体中别无选择地实现,在群体中斑驳陆离地涵概,只能如此,千古如斯。
但势利毕竟为人类美好的道德愿望所诟病,势利者走上层路线时决不敢明目张胆,被收买时也决不会明码标价招摇过市, “有钱能买精脚鬼倒上皂角树”也毕竟只能买“鬼 ”。一则当代民间传说版本说,局长的父亲死了,花圈挽幛一大堆极尽哀荣;局长死了,身后冷清凄凉有加。人们在滚滚红尘与厌厌利欲之中,毕竟还保持着清醒论辨着是非,人与人不带世俗交换的交往毕竟可贵,而势利无论古今决不会立起道德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