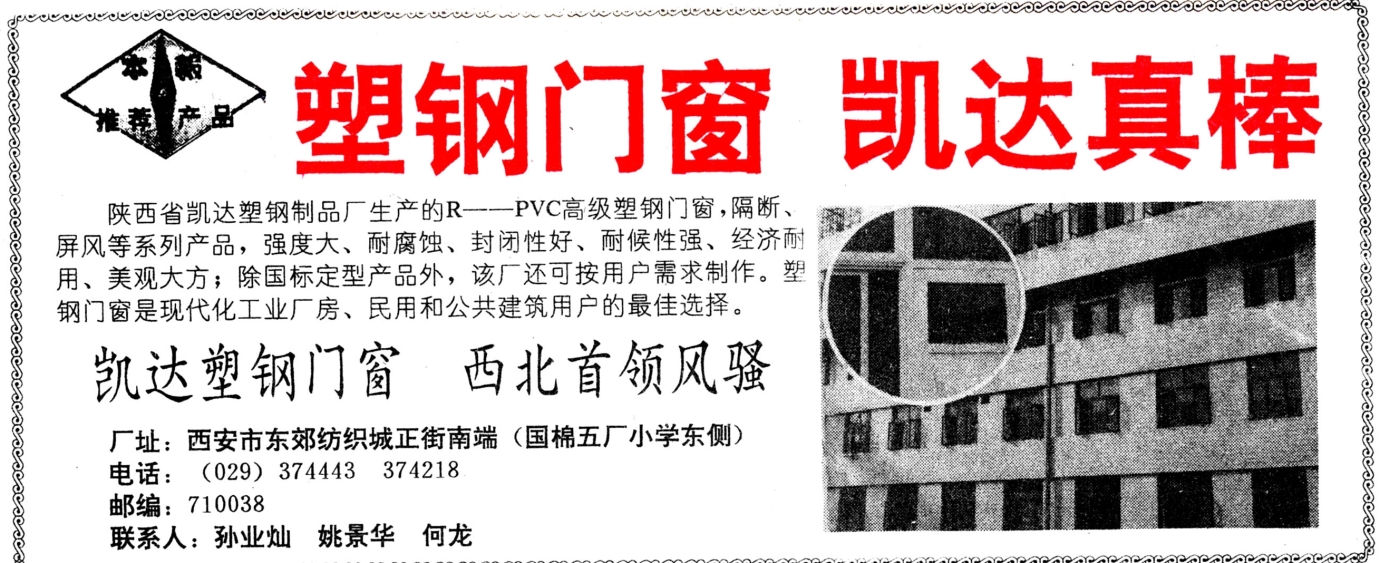本报记者 田勇刚 □本报通讯员 冯炜
甘肃,是我国最贫困的省份,全省88个县中有66个县的财政极其困难,制约其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缺水。
1987年初,国家计委正式批准了甘肃省申请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修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自流灌溉水利工程——引大(通河)入秦(王川)工程的报告。这项工程穿越祁连山脉,总干渠全长86.94公里,是我国施工难度最大的水利工程。
1988年底,来自日本、意大利、中国铁道部、甘肃省的10余支建设队伍集结在祁连山下,在大通河畔拉开了战线。铁道部二十局三处二段作为“中国队”的主力,在“龙头”地段承担了国际标一组和国内标二组共14.32公里的隧道开挖及其附属工程。
在大通河畔的一间简易工棚里,彻夜不熄的灯光下,铁二十局副局长、“引大入秦工程”的总指挥唐万夫,双眉紧锁,思绪万千: “菲迪克”条款集严肃性、周密性和科学性于一身,并对投资者、建设者和工程验收者实行严格的三权分离,这分明是向传统的施工方式提出的严峻挑战。同期中标的国外施工单位,凭借先进技术和精良设备,摆出了咄咄逼人的架势。老唐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他暗下决心:骑虎不下,背水一战。
段长宋宜田带着先遣队风尘仆仆地从大秦铁路一期工程的工地上赶来了,迎接他们的是险峻的山峰、咆哮的大风和变化莫测的天气。没有伙房,他们就背着铁锅,走到哪吃到哪。渴了,喝一口山涧流水;困了,躺在悬崖下打个盹。早晨凉水洗脸,晚上冷水洗脚……数月的辛苦终于为大部队创造了较好的施工和生活环境。
朝鲜族副段长朴光善在家乡延边有个舒适的“安乐窝”,妻子金星子也有份理想的工作。家人多次劝老朴调回吉林,可他不仅自己没走,反而把妻子调进了条件艰苦、时常流动的工程队,夫妻双双战斗在引大工地上。
由于工程标价低,一次性投入很大,国际标计价周期又长,加之部分地质状况与原设计不符,造成机械损耗十分严重,使工程资金显得异常紧张。为了确保工程资金的周转,职工往往四、五个月拿不到工资,最长的达7个月之久。没有钱买饭票,只好到司务处借,全段的借条集中起来有一米多高;没有钱买肥皂、牙膏等日用品,便用工作证到商店抵押。工人曹积润的爱人和孩子在农村,依靠小曹每月寄生活费,可到引大工地后,小曹的钱越寄越少,妻子怀疑他有了外遇,便从千里之外赶到工地,找队领导要求离婚,队领导反复做工作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面对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二段的广大职工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利弊得失,而是国际声誉和甘肃省几百万亩干裂的土地及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农民。他们坚决地提出了“决战引大,打着红旗下山”的响亮口号。
在办公室,在掌子面,从指挥员到炊事员,从风枪手到机械司机,每个人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为抢修高压水管、用身体堵住漏洞、浑身冻成了“冰棍”的侯怀绪,一人开两台车,连续工作42小时、在吃饭时睡着了的郑志闪,三过家门而不入、为单位挽回十几万元损失的何宗信,刻苦钻研技术、给洋设备动手术、为单位节约数十万元的郭来光、陈富忠、吴子印……实在说不尽,道不完。在这里,人们真正理解了筑路工“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深刻内涵。
现在,他们承担的引大入秦工程总干渠国际一标和国内二标的7座关键性隧道洞已分别提前25天和225天胜利贯通。
甘肃引大工程指挥部的领导在验收工程之后,又将10公里隧洞的衬砌任务交给了他们。引大指挥部书记景维新激动地说:“工程让你们干,我们非常放心!”
世界银行代表、监理工程师帕尔默先生满意地说:“在这样艰苦复杂的条件下,工程干得这样快,质量这样好,确实了不起!”
英雄业绩历史不会忘记,因为有奔流不息的大通河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