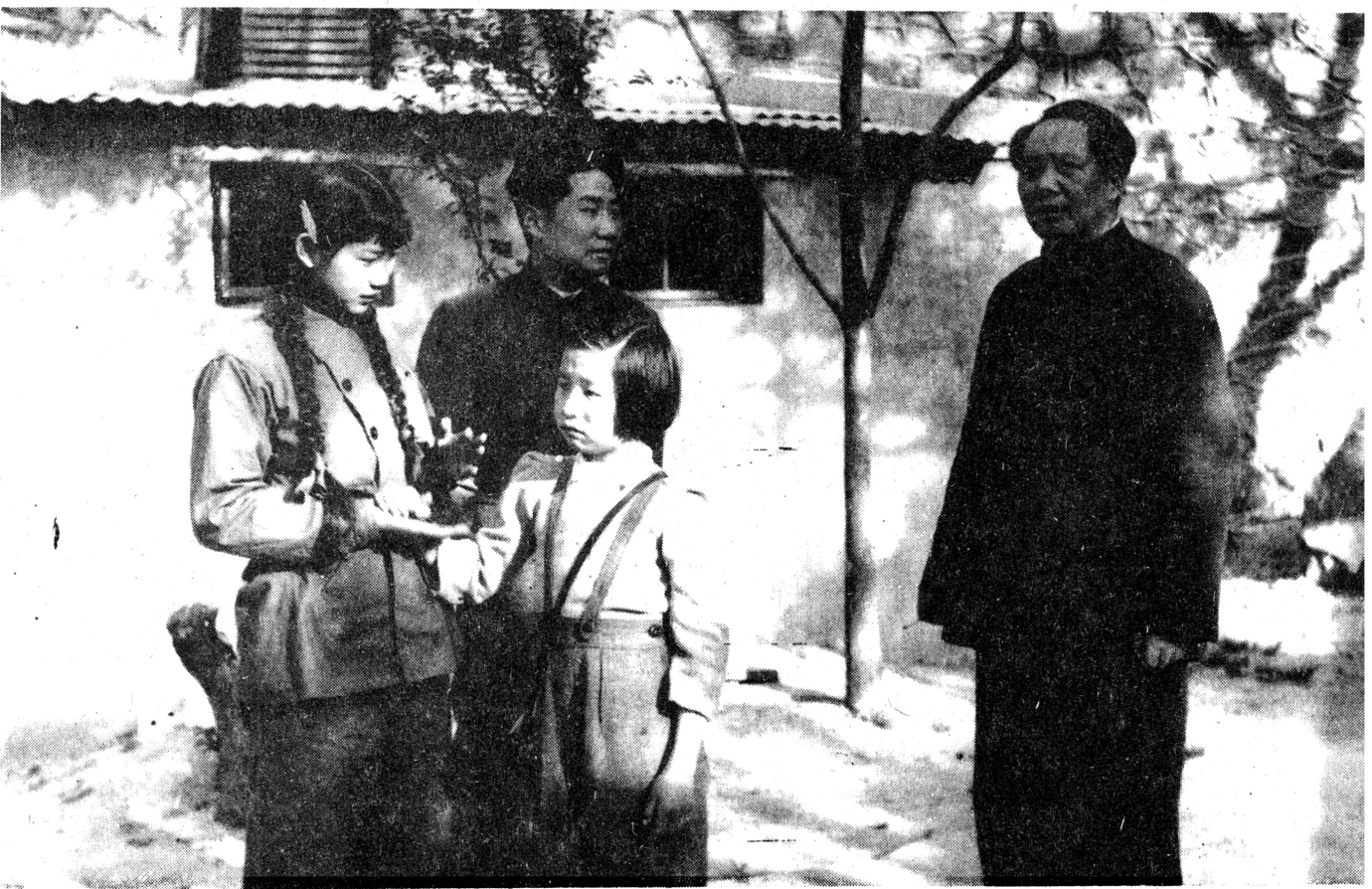肖建国
衣食住行,穿衣是人们生存的第一需要。社会之进步发展,穿衣又从保暖遮体演变为兼有美观、表示某种身份、展现个人喜好和气质修养之功效,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花费于此的精力、财力与日俱增,方兴未艾。而我提起穿衣二字,却是愁从心来。
本人与新中国同时诞生,故家长以建国二字命名,以祈望我此生与祖国一样幸福。当我戴上红领巾那年,自然灾害降临了,饱受了饥饿之苦。以后虽渡过了难关,但家境清贫,粗茶淡饭,所以一直到参加工作,身体瘦弱,那时穿衣多为父亲旧衣改制,膝盖、衣袖处补丁累累,好在当时提倡艰苦、崇尚俭仆,本人也引以自豪。
在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那年本人成家得女,三四十元的低工资,买奶粉白糖花去不少,穿衣自然省之又省,随便凑和,穿件的卡蓝中山装已是侈奢了。
改革以来,收入颇丰,家道渐富,新潮服装层出不穷,按财力所言,实可去买几件时装潇洒一番。谁知还是难遂心愿。
不知是不是多年营养不良的身体突然经常“端起饭碗吃肉”,还是我乃贫寒子弟容易满足,不会“放下筷子骂娘”的缘故,所以几年之间心宽体胖,肚皮渐起,大有与将军肚、啤酒肚试比高之势。体形剧变,原有的衣服当然淘汰,妻子便陪我上街采购新装。谁知如今服装市场虽然繁荣,但规格型号并不多样,且多是套装、大为南方出产。没有一件衣服为我合体,不是臀部太紧,便是腰围过少,再不就是裤腿太瘦,行动难以自如。大约服装皆以南方人身材为标准吧。无奈之下,只得放弃买成衣欲望,买布料找裁缝做。
买布料又谈何容易,如今国营个体柜台鱼龙混杂,古怪名称的布料眼花缭乱,本人又非纺织专家,如何识得全毛与化纤,真丝与麻纱的区别,以至错把涤纶当全毛买回,夫妻互相指责对方无能,上当受骗。后又听得城外布匹市场货真价实,购者如云,于是夫妇又一同前往。谁知市场早已盛行侃价,所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方能购得物美价廉之商品。我苦受市场繁荣物价稳定这类宣传影响日深,哪里谙熟讨价还价云山雾罩欲擒故纵虚虚实实之真谛,羞答答底气不足地请求降价,对方减去零头便心中窃喜,当下成交。未出市场问得别人购价,顿觉吃亏不浅,悔之不迭。所以未穿新衣已减去几分兴致。
买回布料便得找裁缝做衣,国营服装店早已专卖服装,来料加工已消声匿迹。好在街头巷尾“上海裁缝店”比比皆是,抱着对大上海的崇拜,步入几家此类小店,与店主交谈,得知皆为江浙、安徽一带农民,只身闯世界,与大上海并无缘份。本人好在并不看重招牌而只重实际,便交出布料量体而回。此后数天,是对新衣的向往,似乎有些孩时盼过年穿新衣的心情,待到取衣时兴冲冲而去,取衣一试,心便凉了半截。那缝纫技术实在不敢恭维,大约是未出师便赚钱心切的小裁缝,不是衣袖扭曲,便是前短后长,或是衣袋位置不正,衣领扣上会使人窒息。只好叫他修改,这种先天不足的基础怎样修修补补难以令人满意,只好忍气吞声穿着蹩足的劣质服装过闹市,只盼得喜悦化为永远地叹息和遗憾。以后接受教训,再换一家“上海”服装店,仍然是难遂心愿,周而复始地重演做衣悲剧。偶尔遇到一家手艺还过得去的小店,再买衣料送去,岂不知江浙裁缝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早已人去室空、杳如黄鹤了。长此以往,我的衣服竟没有一件做工精细合体笔挺的礼服,一次拿着请柬穿着劣质服装去某宾馆出席一招待会,竟遭门卫盘问,而那些衣衫华丽者却昂首而入,畅行无阻。令我顿有自惭形秽之感。
唉,何时不为穿衣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