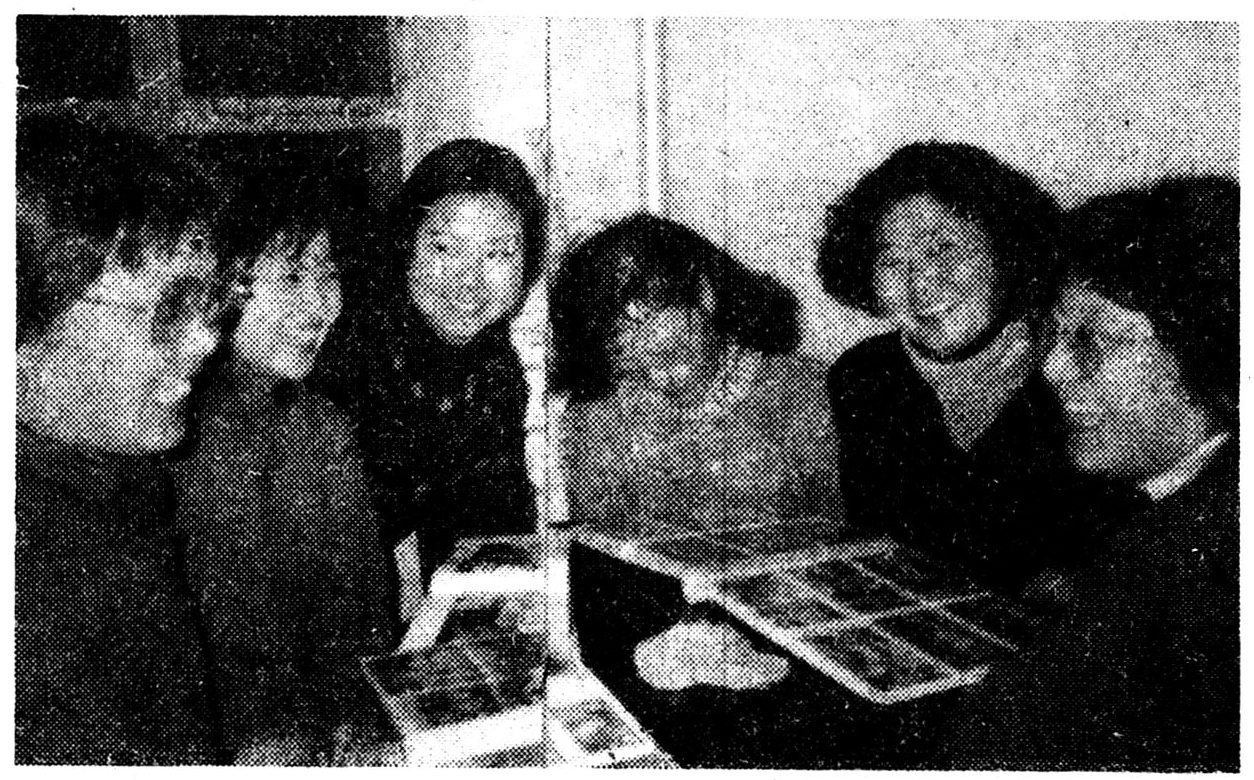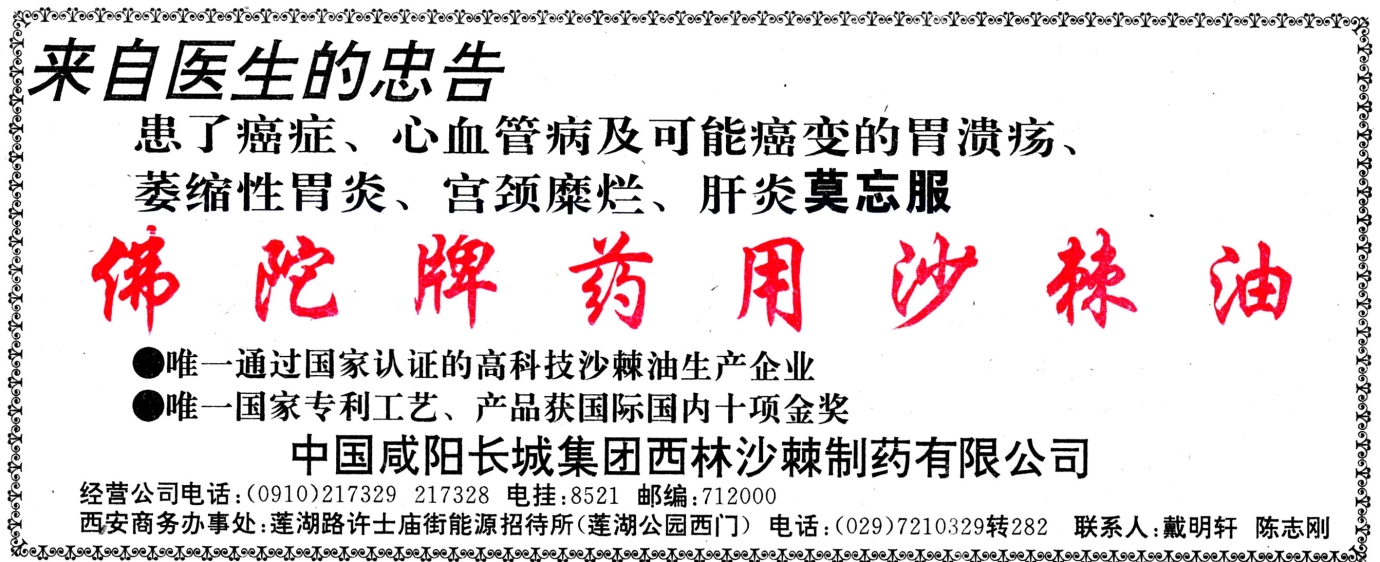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郭沫若曾经感慨万千地说:“《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都由我自己校对了几遍,但终不免仍有错字,深感校书之难。”
陕西人民出版社校对科的同志们在这平凡而又艰辛的工作中默默地奉献着,有人曾经算过这样一笔帐:社里每年要出版新书400多个品种,1亿多字,每本书按3个校次计算,那就是3亿多字,按32开本排出校样,重叠起来,五六十米,相当于两座钟楼的高度!每人每月少说也要看七八十万字以上,远远超过50万字的定额,由此可知道她们肩负多大的责任啊!
其实,校对工作远不象“照葫芦画瓢”那样简单。看校样时间一长,头晕眼花,但你还必须以高度的警觉时刻地搜寻那些夹杂文中的错别字!至于音异字同、字同音异、字形相近、版式版样、字形字号、加条加空、接排另起、明码暗码、背题掉角等等更是多样复杂,来不得半点马虎。加班加点,没黑没明地干已成校对科习以为常的事。不管谁家住近住远,中午都很难回家吃个悠闲饭。一年中,绝大多数节假日,星期天,她们都是陪同校样度过的。她们每人都有一个大挎包,专门为下班背校样用。1993年春节前夕,杨莉随丈夫和女儿回宝鸡给公婆拜年,除了礼品外,还有一包校样,担心公婆不理解,她解释说:“书是要按计划出来,不能因为过节,就延误出书时间,所以在给您二老拜年的时候,也只好背来这堆‘礼物’……”这便有了“背着校样拜公婆”的笑谈了。
一本书,从作者手中送到编辑手中,加工审稿,由于多种原因,书稿仍然难免有错。这就要求校对,不仅照着书稿看校样,还要注意随时发现书稿中编辑没有发现的问题给予纠正。多年来,校对科同志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她们常常不厌其烦地找编辑和作者,将发现书稿中的错处指出纠正,受到作者和编辑的赞扬。省文联的黄河浪同志有一部30多万字的书稿,出书前虽经他反复校对,付印前校对科的同志还是给他纠正了300多处差错。书出版后,他首先拿来一本书,在扉页上书写“火眼金睛”四个字赠给了校对科。陕师大一位教授写了一部长著急于赶印,他本人校对多遍确认准确无误,希望校对科签字付印,校对科的陈虹还是按规定加班加点校对。当他急不可待登门时,陈虹交给了他有200多处差错的登记表,老教授瞠目结舌,深鞠一躬感激地说:“有智不在年迈,我向你们校对科同志致敬!”这倒教为作者负责、为读者负责的校对女士们不好意思起来!
去年,该校对科的6人全部获得陕西省“优秀校对”称号,其中有5人获得二、三等奖,冯小雯夺得全国个人二等奖,陈虹夺得全国个人三等奖。校对科还先后被授予省“八五立功竞赛标兵”“三八红旗集体”等数10个光荣称号。 (赵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