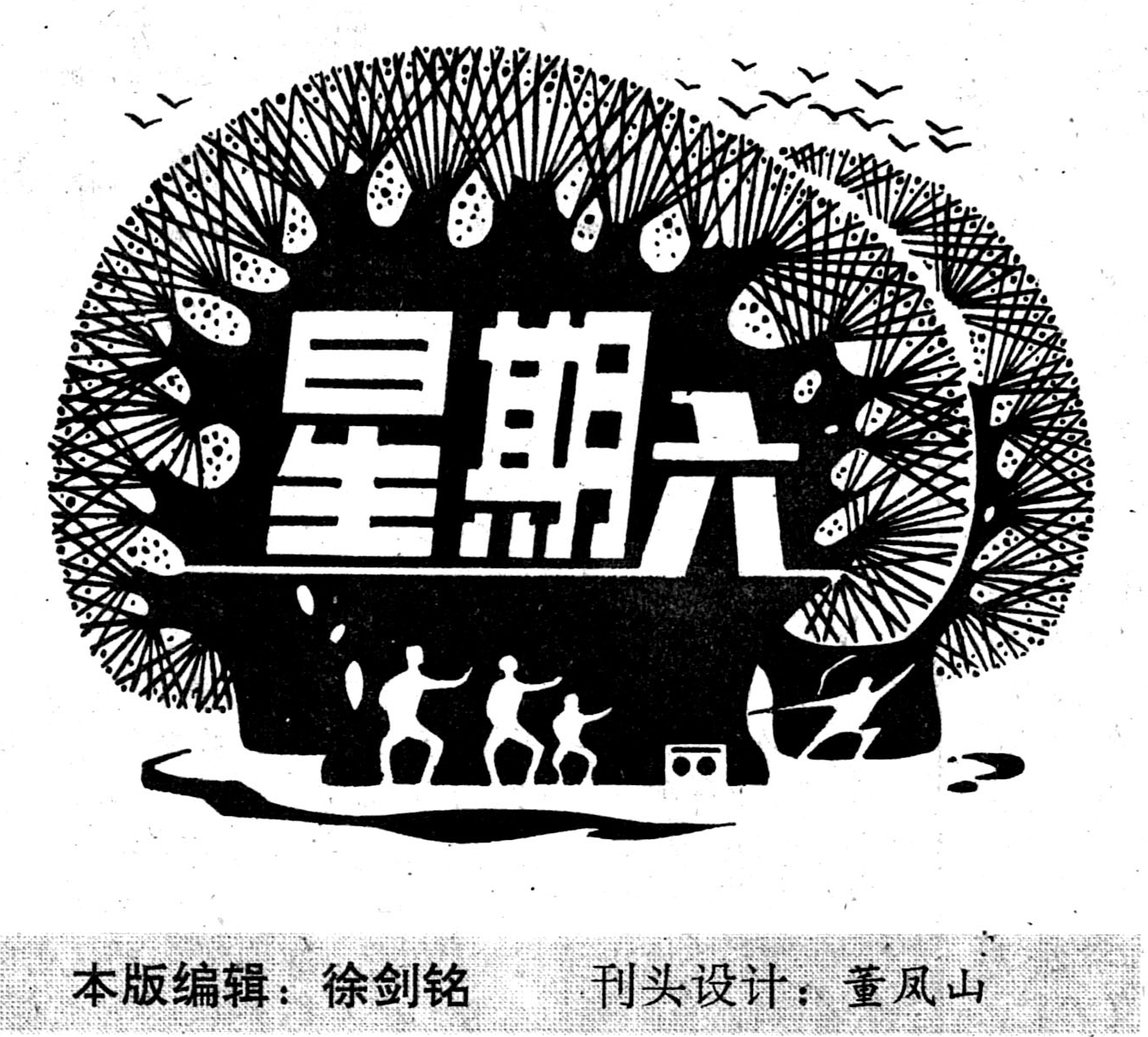文/郭义民
灞河水九曲十八弯,湾里养育着一个不大的小镇,名日新筑镇。街南不远处,有个小村庄,人称“灯笼村”,这儿便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了。
小时大人常说:“家有万贯,不如薄艺在身。”因了这传统观念的滋养,灯笼村的孩子个个心灵手巧,从小就学会了做灯笼。鸡灯,羊灯,盆盆灯,火蛋、兔子、碌碡灯,其中历史最久数量最多的,当数红绸子做成的“长命富贵”灯了。别小看这些小本生意的苦营生,有了它,便有了盐,有了油,有了娃儿的小鸟般的笑,也圆了老人们饿不死的梦。
上小学的时候,村里的灯笼已经很有些名气了。年关一到,整个村子红火起来。平素凄清空寂的农家,一下子有了生气,被五颜六色的花灯塞得满满登登。简陋低矮的农舍变成货栈,炕上放的,地上堆的,墙上挂的,木楞上吊的,少则几百,多则几千,汇成灯的世界灯的海洋。过罢除夕,外地的灯笼小贩便踩着灯笼村青烟未尽的爆竹碎屑进村了。村里人将一个个头上挂满霜花的小贩迎进家里。那时村风淳朴,不兴漫天要价,卖主讨价不高,买主杀价不狠,生意很快成交了。过完数,付过钱,小贩的不敢怠慢,即刻回程。于是满载灯笼的小毛驴车、自行车、三轮车,疯也似地冲出村去,恰似彩河横溢,哗啦啦流向他方。眨眼之间,远处,近处,大村,小镇,到处都有灯笼村的杰作,任红男绿女去挑去检,将吉祥带回家去,为亲友送去欢乐和祝福。因了这灯笼,年便有了年的滋味,也便有了灯笼村的荣耀。十里八乡的人看红了眼,也依葫芦画瓢,干起这苦营生来了。但大多不得真传,不仅做工不细,且数量不多,为讨个好价,常有冒名之事。“哪儿的灯?”“灯笼村的。”脸不红,心不跳,买主也难辩真伪。
春节在忙碌兴奋中过去,村人吁口长气,揉揉熬得红肿的眼睛,清点各自的钱袋,买过之后,少不了一番的感概:唉,咱灯笼村硬是在这苦水里头泡出来的。妈妈却说:是咱的泪花儿养出来的。
做灯笼费事,一只灯笼要过数十道手续,小钱全靠汗珠子去换。灯笼不比其它东西,村人称作“年撂”,倘若当年的正月十五前卖不出去,就剩一个字“撂”了。所以,做灯笼的日子里,家家无闲人,大人有大人的活计,小孩有小孩的用场。文革那阵子,今个“破四旧”,明个“立四新”,刚刚割过你的“尾巴”,又要挖你的“私根”,吓得人像个龟孙子,大气不敢呵一口。可灯笼不做不行,于是明里不敢偷着去做。灯笼做下就得卖,想卖还得玩花招。将“长命富贵”改为“斗私批修”,将“长命百岁”换成“革命到底”……借此以招摇过市。
数以万计的灯笼,小贩能买多少?剩下的还得自谋出路。年关将至,西北风刮得像鬼叫,村人早已沉不住气了,女人和家里的老小留守大营,继续做没有做完的活计,男人则披挂上阵,到远远近近的村子里寻找买主。记得有一回,我跟村里的几个大人去城北卖灯笼,走的是河西那条近道。河上有一独木桥,走在上边摇摇晃晃,吱吱扭扭,未曾迈步,腿肚儿先打起颤来。时值半夜,黑灯瞎火,大人过去了,我却心一慌掉进河里,幸亏大人相救,才保住这条性命。
而今灯笼村名儿依旧,只是村人不再稀旱那些劳心伤骨的苦营生,做灯笼的人家越来越少了。眼见灯笼村徒有虚名,不知长眠于地下并为之奋斗过的列祖列宗,面对村里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新楼,又有一番何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