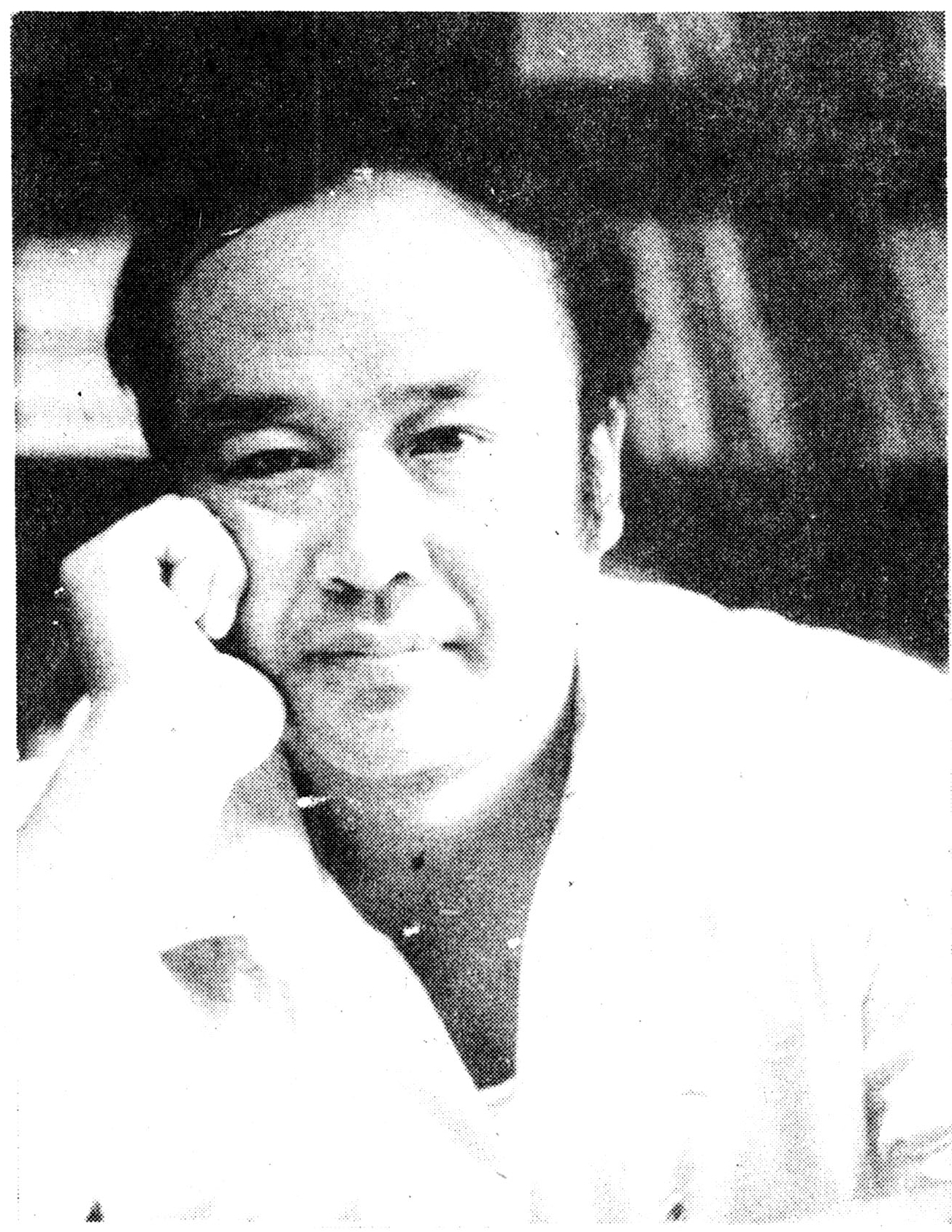文/夏坚德
初识莺歌,我们只有18岁。只为她那两条很长的辫子,我就成了她的好朋友。辫子长得就象她的毅力,为了毅力我同她好。好起来她总问我,咱俩谁大?她说她是2月21日生人。我想想就说,我妈孩子多,她告诉我,我是57年打雷那天生的。莺歌常为我奇思怪话感到我好玩。
分配工作那年,莺歌去了银行,都说她是掉进了金窝。我去了杂志社,也不错。我们相约要在工作岗位上再深造,一边干一边上电大。莺歌的母亲不同意,人怎么可以一心二用、专心才有专长。莺歌从此考试不断。连考三年才上了大学,毕业后又考两年上了研究生。从西安去了北京。她来信讲北京很大,人太渺小。北大给她一颗更远大的心,她毕业后又去了德国深造博士,两年后再考博士后,直到今年,她才学习到了一个句号,终于有了回国来探亲访友的好心情。
弹指20年,军之不去的是旧情谊。我陪莺歌重游古城西安,她说就象在漫游一个大的农贸集市。她问我在这“集市”里生活得是否快乐?
回想1964年随父母从广州迁来时,黄沙、尘士、烈日与冰雪曾让我痛苦。但经过干部下放,经过知青下乡,经过乒马俑与法门寺的开发,还有历史博物馆的建造,几出几进,又几迎几送,西安对于我已有一种故乡的感觉。我在这里安家生子,接待四方来客。我从这里出发去全国各地采访,也去美国考察。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工作一边生活,的确快乐有许多。而这些快乐,全来自于我是西安人。
莺歌问我是否还爱唱歌?她想听。我就带她去“猫王”,去“兰梦”,去“中国城”,去“阳光”,还去“田园”、“鹊桥”和“红楼”……莺歌十分感慨:岁月隔膜,离间了多少乐曲,让她恍如别世。真是一段歌潮一段时代。没有在这一段中生长,音乐就成为陌生。莺歌讲有一次在德国听人奏乐高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虽有准确的音符,却缺乏了陕北乡土民情的风腔俗调,让人听起来怪怪的。
16岁的儿子一声“阿姨”,让莺歌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她这些年埋头学习,不曾想到一个小人落地成长已变成高大英俊的少年了。同是40岁的女人,该是事业家庭果实收获的季节,莺歌却叹息自己是工作家庭两茫茫,一切都还在起跑线上。初到德国,慕尼黑的夜风秋寒袭面,她的左脸部僵瘫了神经。现在笑起来,还一半高兴一半抽着,很不自然。女人成家无足轻重,生子则是重大的飞跃。
“我失去的东西太多了。”莺歌抚摸着我儿子的头喃喃自语。
我咽下想劝她结婚生子之念。人各有志,为志所失,总有所值。抽烟可以成瘾,学习可以上瘾,贪玩可以过瘾。活着,本无模式可循。一切随志走,随缘散,谁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