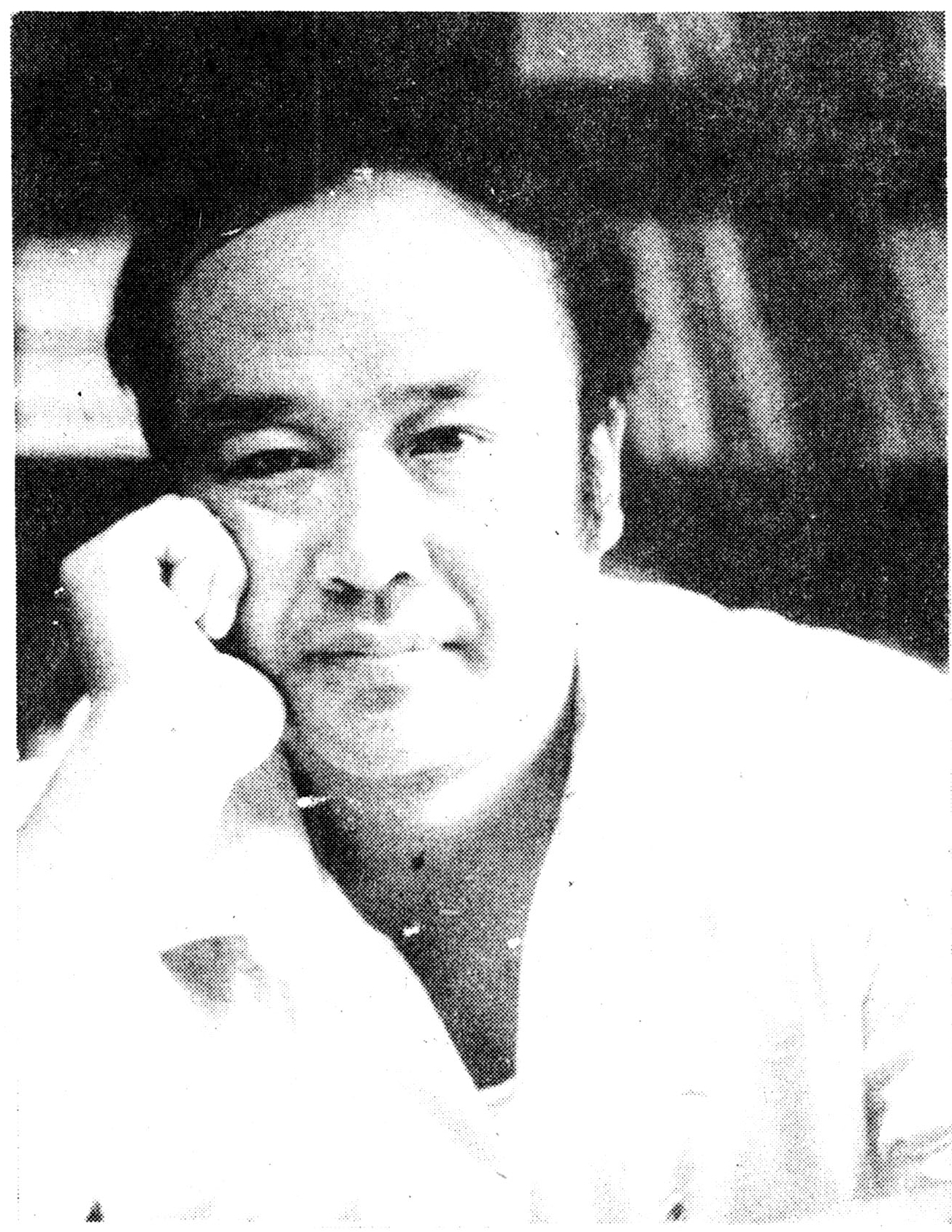文/陈孝英
陈忠实就任省作协主席时说过一句话:“文学依然神圣。”
“依然”二字,幅射悠远,蕴含无穷。
我想仿拟过来改名:“翻译依然神圣。”
其所以依然保留了“依然”一词,是因为当今确有人认为翻译工作未必有多么神圣:既未必有多么重要,又未必需要多少才华。
这是忽略了起码史实的结论。翻开中国现代翻译史,马列主义和西方文明的火种,是鲁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冯至等一大批作家兼翻译家传进中国的,鲁迅对其高度评价,喻之为“普洛密斯士偷火给人类”和“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俄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欧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热情呐喊,奥林帕斯诸神的轻歌曼曲,都是通过翻译的扬声器传入中国的。假使没有翻译,中国也许至今还不知道《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如果没有文学翻译,我们也许时至今日还不认识唐·吉诃德、哈姆雷特和保尔·柯察金。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果戈理同名小说之渊源,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中舒卡尔的形象对周立波刻划《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的启示,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对郭小川的影响,都是中俄文化交流史上脍炙人口之佳话。
新时期以来,随着国门大开,文化、经济、商贸、旅游、政治、军事多方面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翻译工作对中国现代化和国民素质提高所起的作用更是日趋重要。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之中,翻译不仅依然神圣,而且更当刮目。
这些本属常识范畴,但有时恰恰是常识反而易为世人所淡忘,忽视、轻视翻译工作不就是绝好的例证吗?
三
忽视出自轻视,轻视则源于“隔”。
在有些人看来,翻译工作者不过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搬运工”。搬运工只需要从事简单劳动的技能(比如查阅词典、懂得语法规则之类),何需创造性?其实,我从自己先后从事创作、翻译和美学研究的切身经历中感到,要做一名称职的(更不要说优秀的)翻译工作者,对其素质的总体要求并不在作家和理论家之下。因为翻译不仅是一门跨语言的艺术,不仅是“把一种语言的作品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创造性劳动”,而且是一种跨文化的传释行为,是“两种文化互通的港口”。翻译犹如一柄“双刃剑”,一面是甲方的语言和文化,另一面是乙方的语言和文化,其终极目标是创造性地完成,同时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双重意义重构。翻译工作者不仅要传达语言符号表层的意义,而且必须千方百计地了解、理解和悟解语言深层的文化异同、思维异同、心态异同等等。因此,翻译家不仅必须是两种语言的专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应该是两种文化的专家。
正是由于深悟此理,老舍才会说出这样的警句:“一部文学杰作的译本若也成为杰作,便与原著同垂不朽啊!”玄奘所译佛经75部,朱生豪和卞之琳所译莎士比亚多卷集,汝龙所译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傅雷所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以及《海燕之歌》(瞿秋白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译)等优秀译本,在中国几代读者心目中,其译者的名字是永远和作者一起彪炳于史册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翻译在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把它作为一门专门的“艺术”和“学问”来进行研究,将它列为“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苏联学者华西里·诺维科夫逐将其列作“文学”的十大专题之一。
四
陕西是中国翻译事业的滥觞地之一。1300余年前,被印度学者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翻译家”——三藏法师玄奘即在长安大慈恩寺新译佛经,写下了我国早期翻译史上光辉的一页。
新时期以来,陕西翻译事业进入了本世纪少有的繁荣期。省译协组织译书、研讨、评奖、办学,涌现出一批有水平、有风格、有影响的老中年翻译家和优秀译著,为中国译协和兄弟省市同行所称道。3月1日,省译协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暨90年代优秀翻译作品颁奖大会;5月17日,将由省译协在西安承办“全国第八次科技翻译研讨会”。我相信,陕西的翻译事业将在跨世纪的同时跨越旧的自我和新的高度。
翻译依然神圣。
译作与创作、科(技著)作将同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