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骋 贾彦俊
哦,孔雀开屏
蒲城发电厂行政办公楼前,冬青碧绿,鲜花盛开,喷泉溅珠泻玉,池中立一座不锈钢雕塑,名日:孔雀开屏。
传说,孔雀是轻易不愿开屏的。因为每一次开屏,孔雀都要经过一次阵痛。所以,一般人往往只看到孔雀美丽的屏羽,而很少看到孔雀为了艰难的展屏而流出血珠般的泪。
蒲城发电厂是西北电管局首家涉外工程,按照1988年10月18日生效的合同所规定的工程总进度,一号机组应在1992年11月投产,二号机组应在1993年9月投产。可是由于罗马尼亚国内政局突变,经济一蹶不振,供货一拖再拖长达4年6个月,致使蒲城电厂建设工期也一拖再拖。
为了促使罗方交付设备,刘长林心急如焚,坐卧不宁,多次奔波于国内有关主管部门呼吁支持。西北电管局多次派遣高级代表团赴罗催货,刘长林首当其冲地成为代表团主要成员之一。
他本人前后6次赴罗马尼亚,多层次地与罗方动力外贸公司谈判,与设备生产厂家协商,甚至到中国驻罗使馆找商务处商务参赞,通过关系与罗方政府直接接触。在进行这些交涉时,他既有礼有节,又咄咄逼人,把一个厂长所能使的和所想使的招儿都使尽了,终使罗方供货情况有所改观。
千企万盼的本应1992年到达蒲电工地的发电机定子、主变、启动变等大件设备,其中主变253吨,于1994年才姗姗来迟地抵达秋雨连绵,寒气袭人的天津港。
刘长林风尘仆仆地赶至天津港。他在蒲电工地感冒数天未愈,长途跋涉又使他病情加重。但他为了尽快使急需的大件设备运往工地,顾不上治病,仅仅只服了一点儿随身带的药,便马不停蹄地穿梭在港务局、铁路运输部门进行协调。那些天,他不知进出过多少个部门,也不知说过了多少话;只有晚上回到住所时,才感到乏得受不了,脸顾不上洗,脚顾不上烫,一头栽倒床上,软得象一摊烂泥。
他心血的挥洒,使港务局决定克服从未承吊过如此重量大件设备的困难,迅速让货船靠港,起吊;铁道运输部门也为此开了承运如此超重、超宽重物之先河,联系国内最大车型D—35车辆装运大件,并通知铁路沿线部门,通力合作,确保大件安全运行。
1995年9月,当施工现场急需的电缆、四大管道及酸洗管道抵达天津时,泊锚等待进港的船只有上百条。为了使装载蒲电设备的船只尽快靠港,刘长林长驱北京,直奔国家计委、经贸委、交通部请求帮助,只用了两天时间便将红头文件拿到手,又赶至天津港迅速组织多方力量,快卸、快装,改用34辆汽车昼夜兼程地赶往工地,为本来就被耽搁得十分紧张的工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刘长林这般忘我拼搏,几位副厂长也助了他左膀右臂之力。为了保证基建工程质量,副厂长韩可义在施工中大小事情都亲自布置过问,重要环节自己参加了才能放心。在1号机冲管中,韩可义吃住在现场指挥部。由于风寒,他感冒得非常厉害,但他顾不上治病,带着药又进了工地。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斜倚在椅背上迷糊一会儿,再三叮咛施工人员有什么事一定要喊醒他。那两年里,他仅仅休息过三天;即使过春节,他也呆在工地上。副厂长王亦奇在1号机组安装中,决定让生产面各专业分批介入施工现场。由于国内没有完全对口的发电厂可供实习,他为此焦虑不安,决定投资研制一台罗马尼亚33万千瓦机组的仿真机以解决职工上岗前的培训。在研制运行仿真机的日子里,他参与了盘面的设计及功能开发。为了解决研制过程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他顶着烈日奔走在热工院与西安交大之间。为了让一部分生产运行人员尽快熟悉、掌握机组性能,他对仿真机研制采取半调试半培训的方式。根据热工院经验,33万千瓦仿真机研制、调试时间需一年,而他们只用9个月,且造价仅是国内同类型仿真机造价的十分之一。经过培训的上岗人员,在1号机组冲管操作中,尽管初次上岗,但他们启、停操作正确熟练,冲管十分顺利,节约油料1200多吨。 (连载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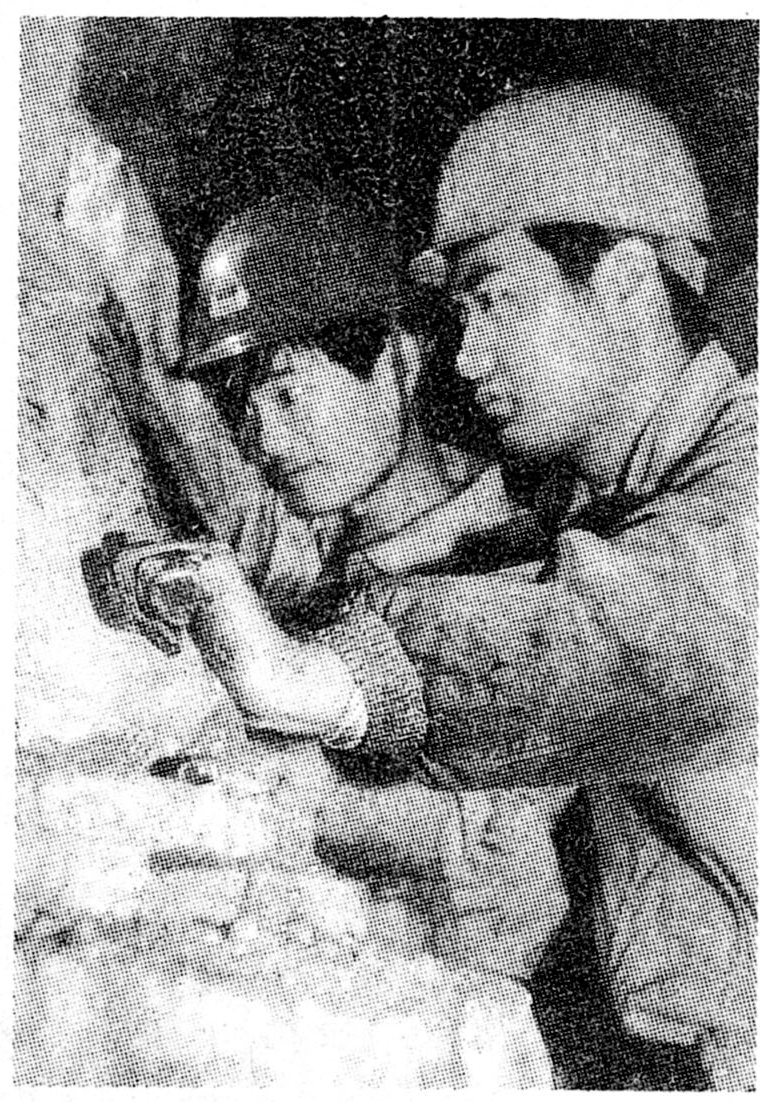
蒲电职工在认真检修消缺。 (申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