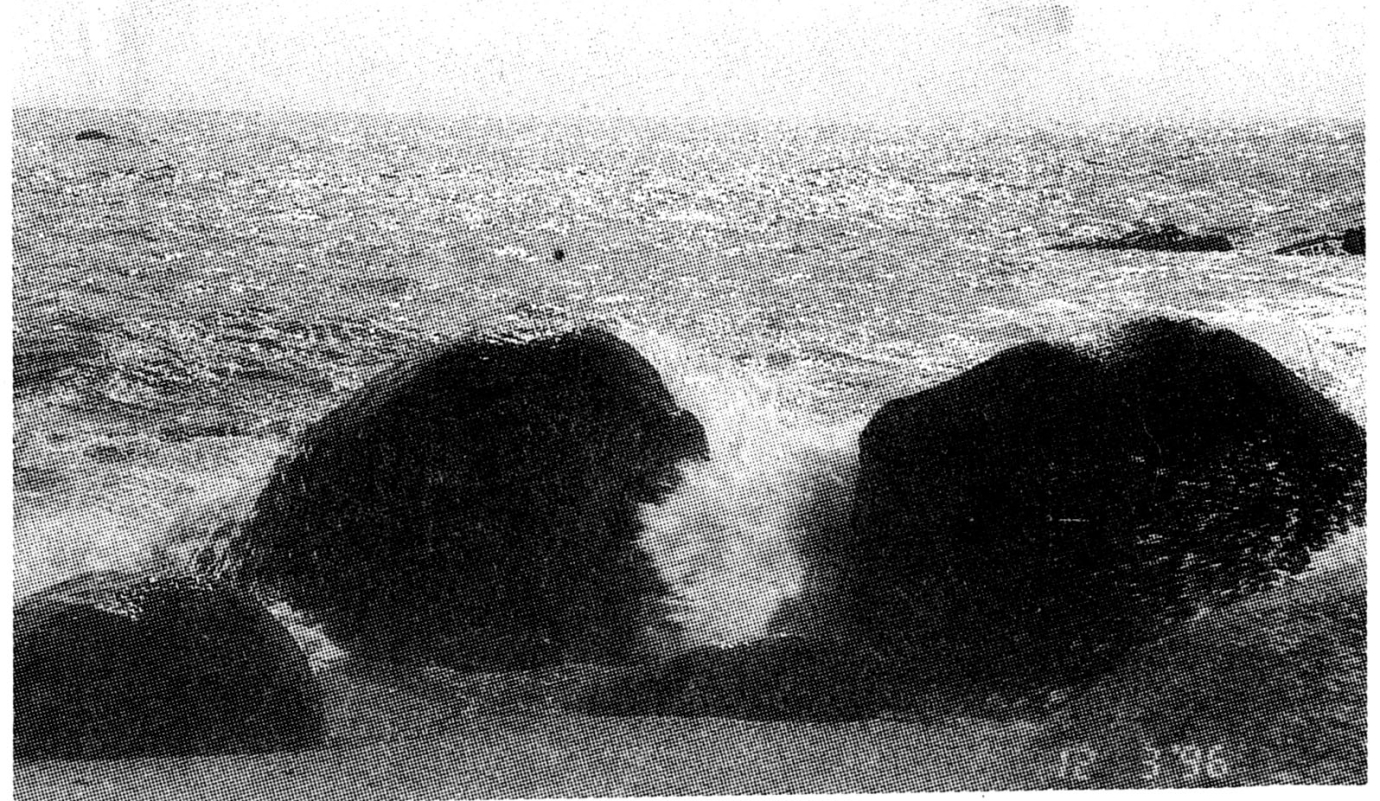孔明
我小时候反感礼貌,原故说出来会令有些人感到可笑。笑就笑吧,我脸皮厚,绝不在乎。本来嘛,我并不知道礼貌为何物,没听过讲座,也没有礼貌学校可上,只是跟感觉学,大人言传身教,我鹦鹉学舌,如此而已,所学也不过一个“乖”字,见爷叫爷,见婆叫婆,长一辈叫姑姨婶妗、伯呀叔的,长一岁也得哥呀、姐呀,然后是“吃咧么?”“喝咧么?”“你做啥呀?”“你还没睡?”“得是看戏呀?”等等,人人这样,就都这样,谈不上礼貌不礼貌。上学后赶上了批林批孔,林孔都是大坏蛋,姓林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流眼泪,背后下毒手”;姓孔的“克己复礼”,开历史倒车。既然“克己复礼”不好,此中“礼”字能好?于是赌咒发誓今生今世不吃梨,看见李子树就绕开去,不喜欢人姓李,谁家办红白喜事,对礼单敬而远之。社会上大刹请客送礼风,迫不急待地跟着鼓与呼。后来又提倡文明礼貌,心里一百个不理解。
有人说:“不讲礼貌行吗?”我就回敬他:怎么不行呢?难道戴个礼貌(帽),像个特务似的,就好吗?谁见过劳动人民戴礼貌(帽)呢?再说了,人不分贵贱,不分尊卑,你不礼(理)我,我不礼(理)你,公平合理,谁不欠谁。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有什么礼(理)可讲呢?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都是兄弟姐妹,若拘泥于礼(理),岂不生分?抬头不见低头见,不讲礼(理),才好和平共处。做人就当实实在在,坦坦荡荡,直来直去,何必在礼貌上兜圈子,不痛不痒的,自寻烦恼?
话虽如此,礼貌还是风行起来。每个公民都被告知:见面要说“你好”,分手要说“再见”;觉得对不住人就要说“对不起”,想客气就说“没关系”;滴水之恩都当道一声“谢谢”,受之无愧也要说“不用谢”或者“不客气”。类似这样的礼貌用语,本应在幼儿园里掌握,不想竟成了成年人的必修课,这是幽默呢,还是讽刺?有人以为这未免小题大作,其实呢?看一看大学校园的厕所里,明明白白写的“大便人坑,讲究卫生”,谁还能笑起来呢?莘莘学子,识书达理,不知作何感想?
有幸生于礼仪之邦,却不幸把礼貌淡忘了,这还不可悲吗?我们还为自己的不礼貌自圆其说:萍水相逢,谁礼貌谁是神经病!男女有别,不礼貌说得过去!大姑娘见客,羞涩地亭亭玉立,谁会把她和不礼貌联系在一起?踩了你的脚,不必向你说“对不起”,谁叫你把脚伸到人家脚底下去呢?骑飞车碰了你还要骂你,嫌你后脑勺没长眼睛!我不礼貌,还不准你礼貌,你越礼貌,我越生气。你说“对不起”就对得起了?我不喜欢听“对不起”,我只喜欢人民币,你乖乖掏了,我只戳你一捶,你不识相,只会用“对不起”搪塞,那我也只有“对不起”了,而且君子动手不动口,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然后扬长而去。你说这是强盗逻辑,是又怎样?存心和你不礼貌,你不服气,也没脾气。
有人也很礼貌,那要看对谁。见熟人礼貌,见生人就顾不得许多了。对上司恭恭敬敬,礼貌有加,对下属却绷个脸,绝不礼貌相向。求人办事,礼貌得令人作呕,事一办完,就你不认得我,我不认得你了。当然,有时候也犯难,自己想礼貌,却不敢。譬如领导向你走来你硬着头皮冒着讨好之嫌,向领导礼貌了一番,领导却昂首阔步,视而不见,你该有多难堪?又譬如你见一位小姐,不礼貌吧,怕失之交臂;礼貌吧,又怕遭受白眼,左右为难,只有碰运气了。
其实,更多的人还不习惯于礼貌,有人甚至真的不知礼貌为何物,你对他礼貌,他反而莫名其妙。你对有的人不礼貌便不礼貌,没有什么不好。有些人不习惯礼貌,却想学,礼貌用语一出口,总是留有尾巴,比如说“谢谢”,很少就此打住,一般都要加一个“啦”字,或者干脆说“谢谢你啦”,让人听了,总感到哪儿不对劲。
我没有出过国,无缘消受欧风美雨,只是偶而道听途说些异国他乡的礼貌话题。据说西方人极是虚伪,开口“对不起”,闭口“谢谢”,无过也说“对不起,无恩也说谢谢你”,直让一些出国留学、观光的同胞心里犯嘀咕:外国人莫非都吃错了药?明明中国人的包砸了你的尊脚,你不回敬以破口大骂已够绅士了,再道声“对不起”岂不太掉价了?
忽然想起了去年夏天,我与曹杨兄游陕南岚皋县,走在落后的乡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岚皋的父老乡亲很礼貌!无论路上相遇,还是打从门前经过,必有礼貌的问候:“城里人吧?”“上山呀?”“歇一歇吧?”“进屋坐,喝口茶!”我与曹杨初来乍到,觉得新鲜。看来,穷与礼貌并不同步。一个礼貌的民族,再穷,也是礼貌的。谁都知道,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从岚皋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古风,更看到了希望!
末了,我觉得有必要画蛇添足:一些人认为的礼貌,其实经不起推敲。比如见人就敬烟,吃饭就敬酒。烟、酒是什么货色,谁心里不明白?既然吸烟有害健康,何必要敬人一烟呢?既然客人有言在先,说他不会喝酒,何必要强逼他非喝不可呢?殊不知,不尊重别人的自由和生命,还有什么礼貌的价值可言呢?
我但愿人们越来越礼貌,也但愿人们不要把陋习当礼貌。把外国的礼貌进口一些,我看没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