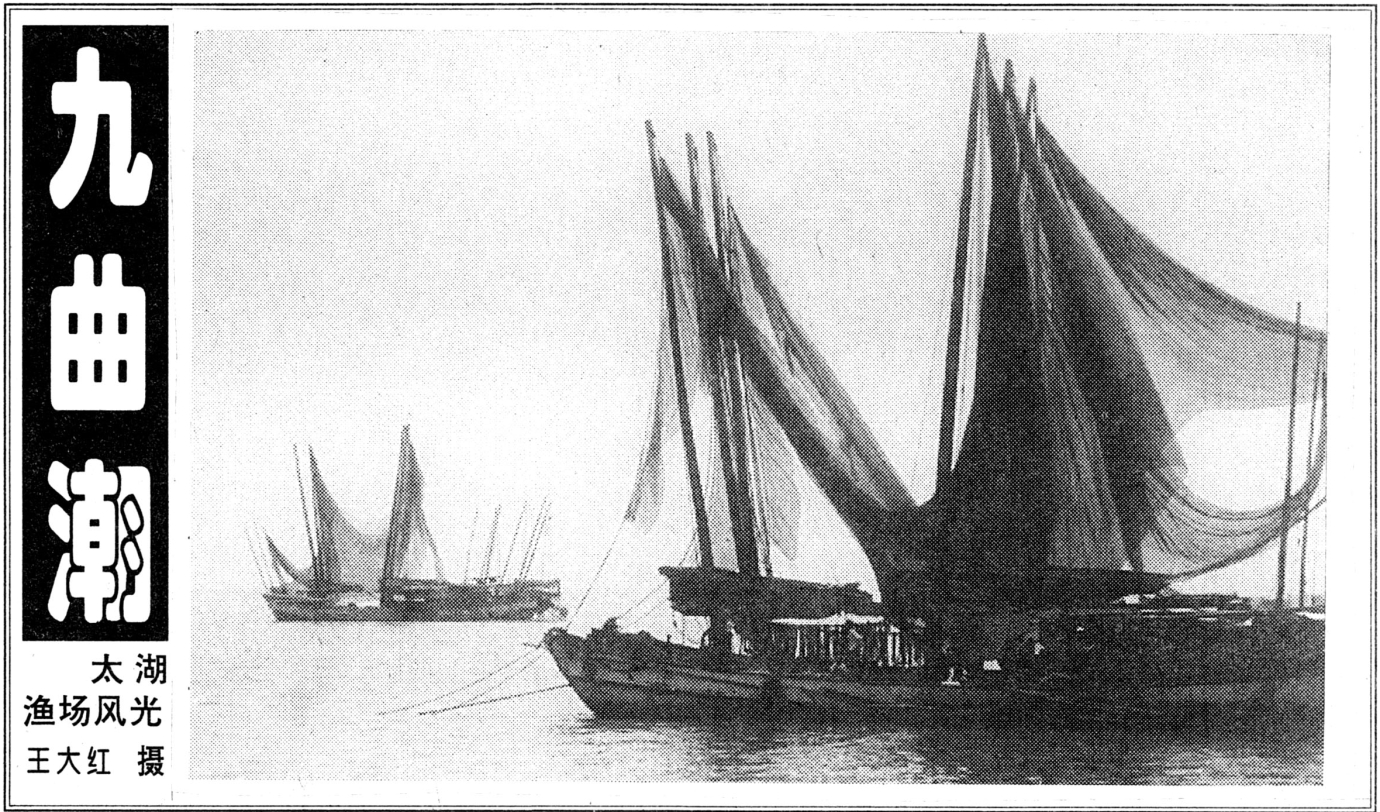文/陈文野
年愈九旬的父亲也许因为年纪的渐老,令我愈加牵念。夜半少不了一脉忧郁袭上心头。每当这个时候,心里便有些酸楚:哦,我想家了!还联想,此刻风烛残年的慈父必定正在想我!父母思念儿子比儿子思念父母更苦。当年他们毅然送我们弟兄走出家门,其结果竟是自己晚年意味深长的、无可疗治的孤独!这是天一样大的牺牲精神啊。
又近腊月,我的脑海怎么也静不下来。原本相约这年的春节就在矿上过,而除夕钟声敲过,第二天一大早,我起床后抹了把脸,就直向火车站奔去。回家走到村头,老远就看见父亲在家门口站着,朝我走来的公路口张望。看见我,父亲就说:“你咋能不回来呀?我昨日把炕都烧热了……”望着父亲瘦削而急切的脸颊,我感动得落泪了。
故乡,是吸引望日莲将脸盘朝它凝望的太阳。每次回到父母身边,父母都要起身相应。父亲点点头,说:“喝口水吧。”便进厨房倒开水去了。他要把亲热的机会留给母亲。母亲总要扯扯我的衣服,即使没土也要拍拍,接着说些听多少遍也不厌烦的话。而近年的回乡,与父母见面,两代人都不免惊讶些,父母的目光慢慢掠过我的脸,必是看到了我的皱纹、白发,又抚我的背,必是有些驼了。父母自己呢,头发已是纯白,且已无多了。父亲说几个字便要停下吸气;母亲站立之前先要揉膝,而后伸手扶墙,扶桌沿,扶孙女的肩,她也跟幼儿一样,需攀扶个什么才能站立,身子才能移动。我与父母彼此打量着,心里都有不想说出的话,“这就是我的父母么?父母就真的成了这个样子么?”多么希望是梦,想见到原先青春勃发的父母,然而不能。就在父母的眼中,儿子不也是原先的儿子了么?“年岁大了,得注意身体呢。不能再那样熬夜念书写书了。”父亲拄着拐仗,说罢一瘸一拐地回他的房间歇息。而父亲对我的叮嘱,却越发令我感到时光的无情紧迫。
我是为见到双亲才归家的,当见到双亲之后,为什么依然空落呢?我究竟是要寻找什么呢?
村中人都说,艰难中走过来的父亲能有这样的高寿,全托他老人家心平气和宽厚待人。细细想来,这话不无道理。
记得父亲不灵便的腿,是那年在公社棉绒厂帮工人干活时被棉包塌伤的。本该不是他干的活他却去帮人干了,后来就落下这终身不便。父亲没有伸手去要公伤补贴。他说得很肯定:“什么待遇,不要了。当年我14岁逃出去当徒工,能活下来就是福。再不要给公家添麻烦了。”
记得那年我出外工作时,父亲叫过我们说:“学会宽容,善待不幸的人或不幸的事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倘若太吝惜自己而不肯为别人让一步道,这样的人最终会堵死了自己的出路而无路可走。”父亲识文断字不多,但他近乎哲理性的语言叮嘱,现在回味我们弟兄走过的路,无不是他这品格的熏陶。
慢慢地梳理思绪,答案终于有了。往昔苦不堪言的事情,和父亲一块低头拉着近千斤重的红薯到西安挨门换玉米面糊口;大雨天和父亲淌过齐腰深的灞水买回蔬菜又去卖掉为换回我的学费;弯腰背袋的父亲步行到四十里外县城为我读书送面送馍的背影,现在回忆起来竟有几份甜蜜,陈年坎坷到了今天就是我坚韧生活的必要营养!这一切儿时的记忆都已化入故乡的土地,唯独父亲留给我们的宽容品质至今仍成为我的立身之本,越是年龄大越是体会这言语的分量。宽容,因其宽广而容纳了狭隘,因其宽广显得大度而感人,比如水一样,以自己的无形包容了一切有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