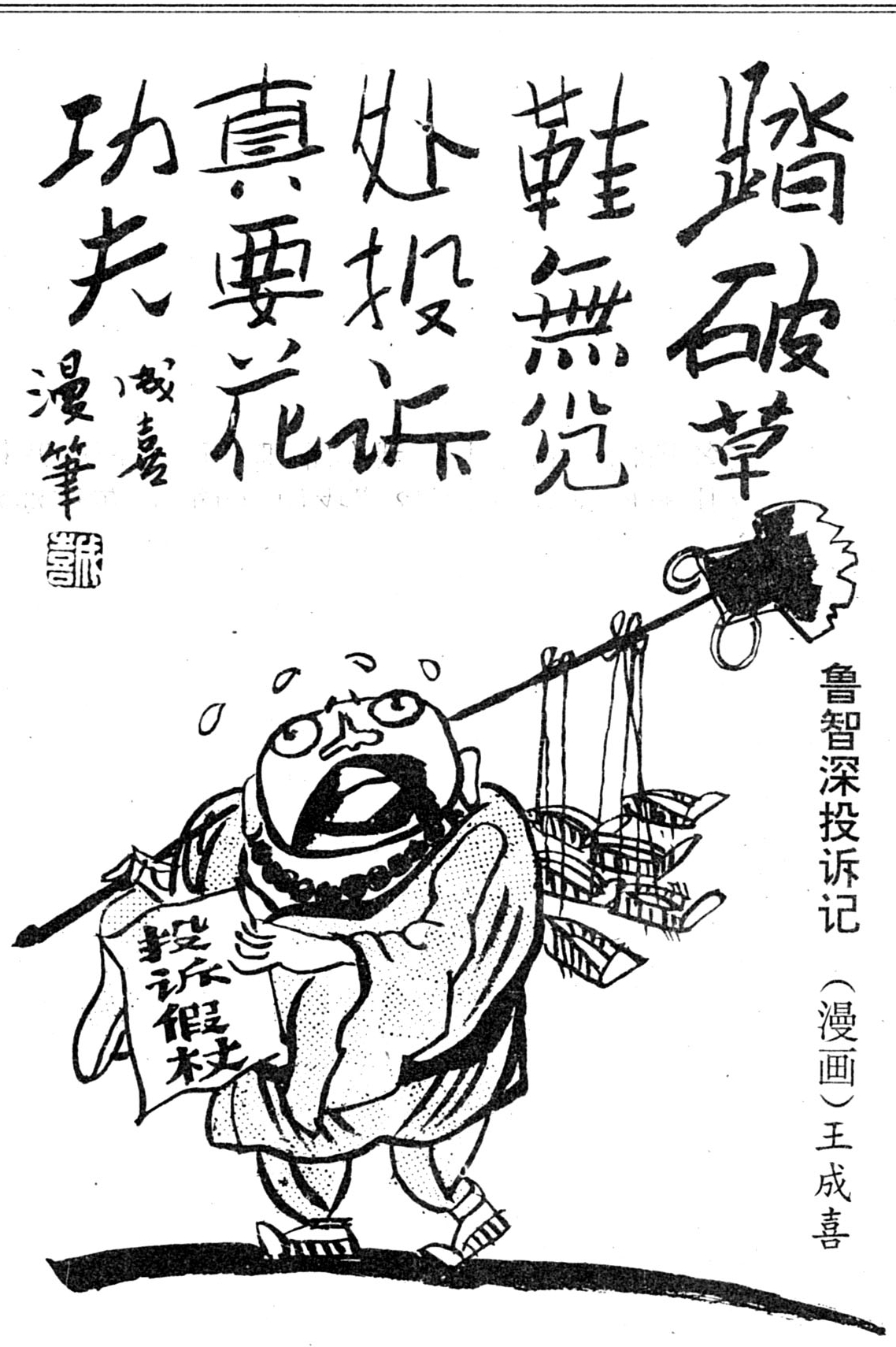文/姜夔
也许是天性使然,也许是长期忧郁苦闷所致,在所有西洋音乐和中国民族音乐中,我对二胡是情有独钟。
二胡虽然没有提琴、吉它那样丰满的和声,却有着极其独特的音色。我以为那音色最适于作幽深的歌吟,绵长而凄迷,煞是扣人心弦。每当静夜临窗,听一曲《江河水》,想起如烟而逝的往事,禁不住就有了潸然泪下的感觉。
其实这种感觉又何止是我呢?就连小泽征尔,如此大名鼎鼎,据说他听《二泉映月》的时候,也感动得长时间掩面而泣。是什么打动了他?是什么让他潸然泪下?是那悲凉的琴声让他想起了并不幸福的童年,想起了去国遁乡别梦依稀的海外漂流。一曲终了,音乐大师泪痕斑斑地抚摸着那两根细细的琴弦,长叹一声:这两根弦,缘何如此神奇?
我正是因为这悲切的音色才走近二胡的,这就宛如我多年以后走近萨拉蒂所赞美过的“孤独的萨克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去倾听刘天华的二胡曲,苍凉的旋律弥漫着、鸣咽着,如泣如诉,我好象走进了一座圯败的庙宇,四周蛛网密布,有几点残香袅袅点燃。我铺下一张破席,躺下来静静地等候黑夜和死亡的到来。这种至悲的情怀是唯有二胡才能给予的,濒临死亡的体验丰富了我的人生,又让我的笔端流淌出许多悲凉的文字。
记得当年羁旅江城,远离家乡的我有着挥之不去的乡愁。那天我漫无目的地徘徊在幽深的小巷里,北风夹着雪花呼啸着,我紧缩在厚重的棉大衣里一脸忧伤。这时不远处传来了比我的忧伤还要忧伤的二胡声。我看到个瘦瘦的老者在颤微微地运着琴弓,双目混浊,脚下的小搪瓷碗里散陈着几张小面额的纸币,那时刻,我突然想冲上去拥抱一下这个不知来自何方的老人,然而我只是无言地注视着他。我只能抛下几张纸币,在呜咽的琴声中悄然而去。
那天晚上因为这份悲凉我为二胡写下一首短诗,里面的两句我至今难忘:“一根弦让我醉,一根弦让我醒”。我何时曾醒过呢?
我对二胡的感觉始于童年,始于鄂东常见的算命先生的琴声。可能再也没有人能比他们更能体味这人世的苍凉了。
再以后这种深切的感觉就是我故乡的一位朋友。当年极具才情的他因为家庭出身而无缘进入大学,只能落魄为“旧帽遮颜”的挑夫。于是,他常常自叹自怜,借一把二胡一诉心曲,我记不清多少次听过他的琴声了。
未曾想到这琴声注定了我和二胡解不开的缘份。我所遗憾的是,在往昔的岁月里,我未能学会演奏二胡。否则,我真想仿效《命若琴弦》里边那个拉断一千根弦的老人,沿着漫漫长途边走边唱,直到生命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