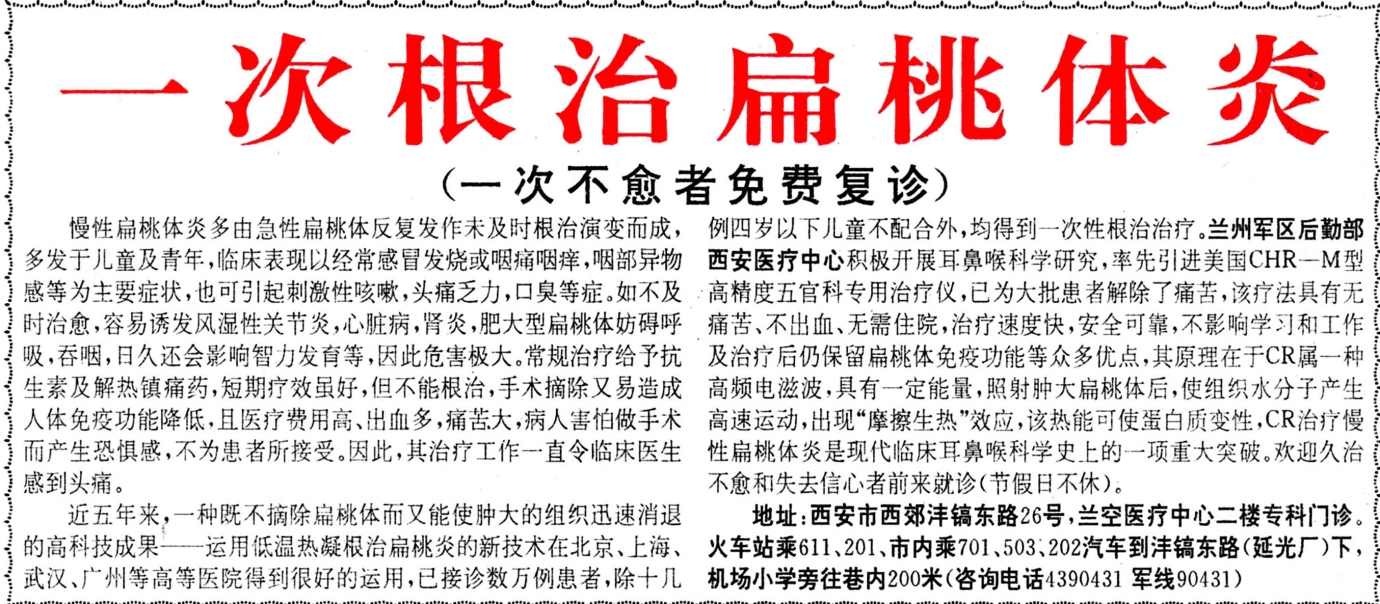文/郭世炎
两年前,由于假冒伪劣品泛滥成灾,消费者深受其害,有强烈的“打假”要求,敢想敢为的王海便独辟奚径,闯出一条前无古人的谋生之路,“打假专业户”便应运而生。既是谋生,当然要有利可图,“索赔盈利”便成为目的和不否认的事实。由于王海高举“打假”的旗帜,便又理所当然地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赞誉之声此起彼伏。各地的“王海”们窃见此举名利双收,便亦步亦趋,纷纷傚尤。不管动机如何,“王海现象”对各大商场敲响了警钟,对净化市场确有一些积极的影响。
然而好景不长。今年5月王海及其追随者组成了“打假公司”,来西安做第一笔生意——追查“健美神药带”造假一案,出师不利。为化解尴尬局面,他们主动出击,频频光顾西安的八大商场,并于7月11日在《南方周末》报上推出王海的两篇新作《我的失望》和《西安日记》。文章反映王海们遭遇冷落的现状,也折射出人们对“王海现象”已有了理性的认识。商业部门已胸有成竹,政法部门和有关领导对王海闹市已感厌烦,社会各界支持王海者日渐稀少,过去的王海热正在化为过眼烟云而风光不再,这不是偶然的。“王海现象”自身存在有难以克服的弱点,名不正则言不顺,或是名正而行偏。王海“打假”不打蛇头要害,偏偏把矛头对准以国营为主体的,有社会威望的,主观上抵制假货因而有“假一罚十”或其他承诺的大商场。他们除了能打倒商家的承诺之外,动不了制假贩假者的半根毫毛。人们理所当然地不再欢迎“王海现象”。
王海是“消费者”吗?
热闹一时的“王海现象”是以“消费者”身份实施“打假”并提起诉讼的,在他的“失望”文中,曾八次使用“消费者”称号,可见王海离开“消费者”名义便寸步难行。但遗憾的是王海的行为已经不是消费行为了,只是一个冒牌“消费者”而已。
王海手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敲开了法院的大门,但该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而王海购实商品,一不为“生活消费需要”,二不“使用商品”,“退赔盈利”才是其动机和目的。所谓“消费”只意味着开支,而王海们的“消费”却意味着收入,世界上哪里有凭“消费致富”的怪事?特别是王海们已经成立什么“打假”公司,便是已具备法人资格的经营行为,凭什么仍以“消费者”名义光顾商场?凭什么指责法院不予受理?凭什么嘲笑“法律为儿戏”?
“知假买假”≠打假
王海们高举“打假”的红旗,否则便出师无名。但有名无实,不如无名。“打假”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个人行为,甚至不是某个部门可以包揽的职能,而是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配合行动的一个综合职能。其中,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者投诉,保障消费者权益;技术监督局检验商品质量和真伪,提供打假的依据;工商管理部门查没假冒伪劣商品,勒令黑窝点关门停业;公安和司法机关则缉拿制假贩假的犯罪团伙,收留在监并量刑判罪。这些权威部门协同作战,才能形成打假的铁拳,布下天罗地网,使假冒伪劣无容身之地。这才是有名有实的打假,岂是一个王海,一个公司,甚至全国各地一轰而起的“草莽流寇”能够取而代之的!
对个人而言,“打假”只是吹牛而已。“打”字何意?乃“打击”之意也。可不是打酱油、醋,也不是打牌、打球等人人皆可为之的琐事,而是属于“专政”范畴的大事。除在“文革”时期有可能被夺权之外,其它时期都不可能,任何个人也不具备“打击”的能量,不具备“打击”的权力和权利。“消”法给消费者的权利为“消费者有权检举、控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有权对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提出批评、建议”。王海们既然知道什么是假货,为什么不向有关部门提出批评、建议,甚至检举、控告?而非要“故意买假?”“消”法给了你“从中牟利”的权利和“打假”的权力吗?
是真是假谁说了算?
王海经过一番调查了解,掌握一些假冒商品的资料,因而有的放矢,常常打中要害,很轻易的达到索赔的目的。但王海们不是一群火眼金睛的孙猴子,一眼便可看穿妖魔鬼怪。虽说是“知假买假”,“以真当假”的事也常有发生,这是王海们屡屡索赔失败的主要原因。当为真假发生争执之时,就必须由技术监督局出面仲裁,这是人人皆知必须遵循的常识,但王海自以为是,是真是假他说了算。他在民生买了他认为的假计算器,民生却拿回了技检部门是真非假的证明,王海竟在“失望”文中指责民生:“振振有词”,“居然拿出技术监督局某质检站准许销售的证明。”请看王海的口气多大,对技检部门的证明嗤之以鼻,视为非法。民生与他的代理律师本来已签订《和解协议》按“不满意便退换”的承诺处理。但在6月26日《中国青年报》关于王海诉讼的文章中说:“王海从西安打来电话,说2月25日曾向他加倍支付了假货赔偿金的民生百货大楼……”竟把“退货”说成是“加倍赔偿”,有意损害民生的形象,借以壮大自己的声威。王海是否诚实信用值得怀疑。
青岛慢怠游子还乡
“王海现象”虽是王海的创举,但并非壮举。各地政府和群众可以欢迎,也可以不欢迎。不可因为有所怠慢便表示不满,便指责人家“腐败”、“地方保护”,甚至出言不逊,将“死猪不怕开水烫”也写进文章,这是否有辱文明?他的家乡青岛对游子还乡竟采取“一不支持,二不反对,三不鼓励,四不提倡,五不报道”的对策,更使王海恼火,不由列为“罪状”表示“失望”。可以认为这“五不主义”是不欢迎的表示,但不欢迎者岂止你的家乡,西安的一些报社也采取了“低调处理”的作法,既未报导王海的活动,也拒登批评的文章。假如没有“五不主义”,不作“低调处理”,潜伏的反对意见得以释放出来,恐怕王海们前途不妙,美梦不长。
王海在1995年发表了《我的困惑》的谈话,两年之后写成《我的失望》的文章,再过两年便可能发出《我的绝望》的感慨。这是不是“王海现象”自生自灭的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