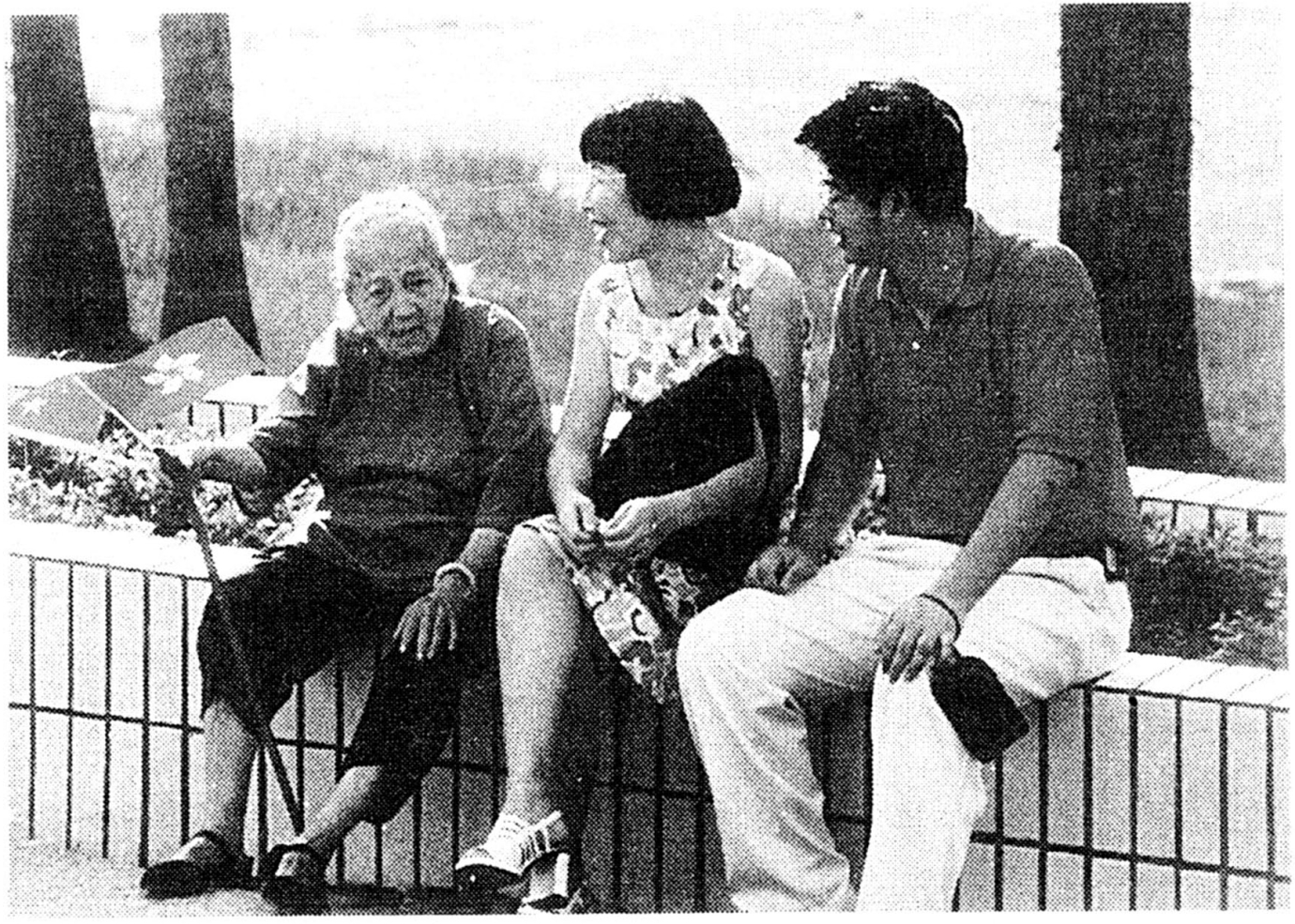文/庞一川
叶落归根对中国人来讲,无论有文凭的,还是斗大字不识的;无论捡破烂的,还是坐高级小车的,全能深刻理解,绝无丝毫异议。
当年我父亲被打成了三反分子,押进牛棚里,五天一大斗,三天一小斗,别说指望平反,生死也由不了他了。但怀乡之情竟强烈地撞击着他。他冒着畏罪潜逃的罪名,他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偷偷地溜回了家乡。
可他仍不敢踏上那白白的羊肠小道,也不敢站在他童年顽耍蹦跳的石磨旁,他深知风景秀丽的小山村,上顿下顿靠土豆哄饱肚子的父老乡亲们,依然如痴如醉地干着文化大革命的买卖。对父亲的外调,对他的罪名,村里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他只好站在高山之顶,遥望着山凹中朦胧的小山村。
当他听见鸡鸣狗叫,听见亲切吆喝的乡音,当他看见袅袅升起的炊烟,他腿一软,抱着树杆跪下了。
他们这代人对家乡的思念和想往,的确叫我嫉妒羡慕,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要将骨灰带回老家呢?要不他们怎么会在弥留之际,喃喃自语叶落归根,叶落归根呢?
我从小到大,从辱到荣,从荣到辱一直在填表,那表上总少不了籍贯两个字。意思是极明白的,告诉人家你的根是哪棵树?我曾看过一幅画,金子般的夕阳,空矿的原野,一棵笔直硕大的树,它的根部洒满了厚厚的、黄黄的树叶。油画的名字叫“叶落归根”。我想倘如父亲看了这幅画,定会思绪万千,泪流满面的。而我最多说一句画得挺不错。
我不知填了多少张表,籍贯一栏写下“山西”二字。从此就有人叫我九毛九了,随后我便熟知了九毛九的典故。
我是跟着父母走南闯北的,在长江流域吃几年大米,又蹦到黄河流域吃几年面粉,可一次也没回过家乡的。文化大革命又随着被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父母发配到农村。据我所知很多人都回到了原籍,而我却和父母发配到了紧靠渭河旁的一个小村庄。命运使我再次错过了体会家乡温暖,读懂家乡风韵的机会。
然而我却并没有感到失落了什么,更没有惋惜遗憾的心情。尽管我从父母的口中多多少少知道点家乡的山水,民情风俗,家乡依然是朦胧陌生的,正因为如此,自然不去想往家乡了。
其实像我这样生在红旗下,长在城市中的一代人,即便他们偶而回过几次家乡,也不过是匆匆过客,对家乡并无太多的情感。有资料表明,80年代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人,挣了钱是想回家娶媳妇盖房。而到了90年代从农村杀进都市的人们却顽强地要在城市生根开花结果了。他们对叶落归根表现的不仅仅是淡漠,而是冷漠;他们不屑于叶落归根,他们牢记“哪里黄土不埋人”的格言,大有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气魄,可敬可佩。
当然无论他们的人生是否辉煌,他们到了中年,到了老年,仍会给他们的儿女描述家乡的一草一木,沟沟坎坎,叶落归根偶然也会泛起,但决不是坚定的,迫不急待的。而轮到他们的儿女也准会像我这样,对家乡,对叶落归根麻木不仁了。
这种现象的确很残酷,尽管残酷,你却不能否认这毕竟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