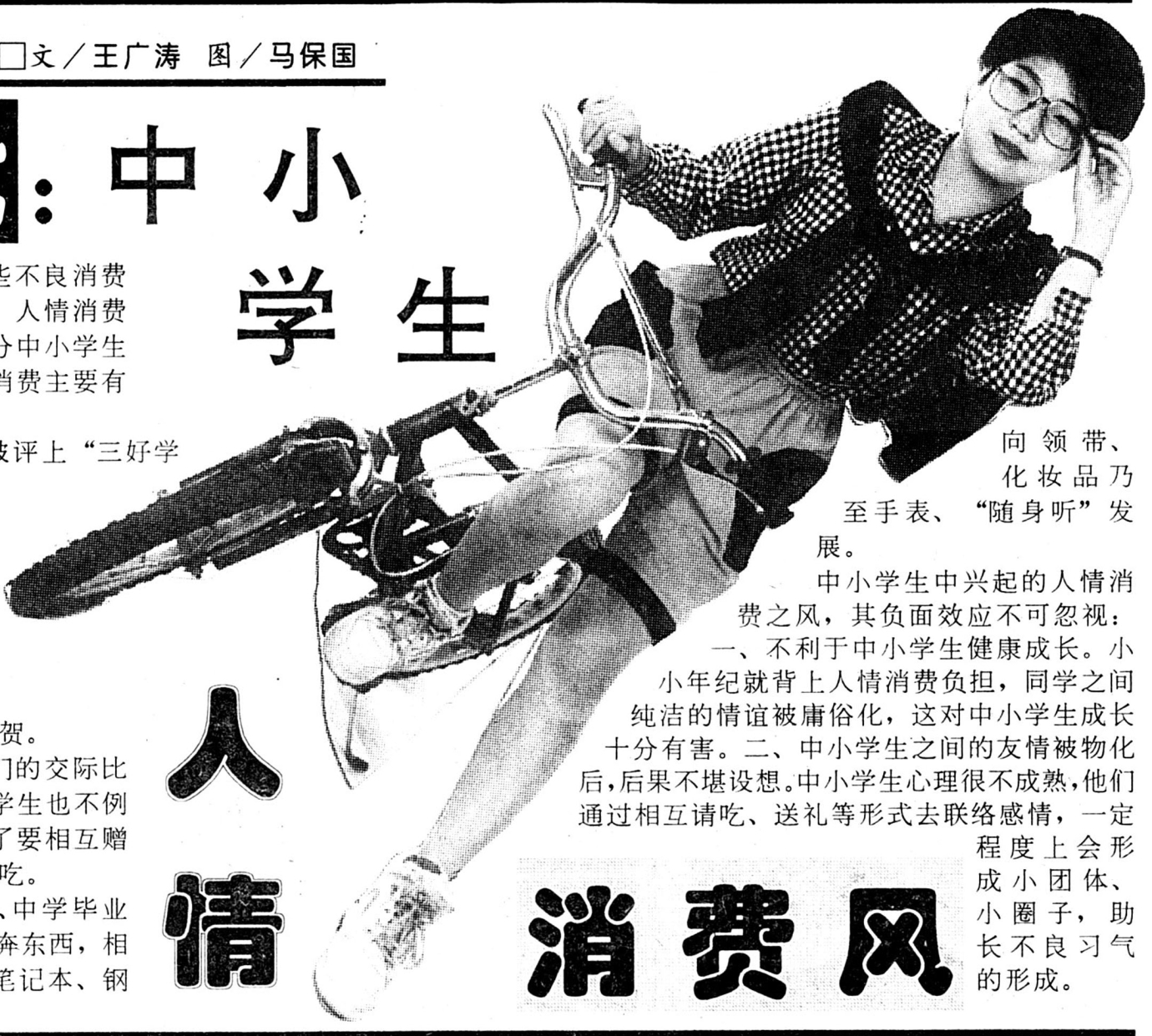文/朱秀
伴着凉风,和着虫鸣,新秋又来临。“天凉好个秋”,是一种秋;“秋风萧萧愁煞人”又是一种秋。秋景、秋色、秋意、秋声,喜秋、悲秋,抒写秋感几乎成了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
古人咏秋多是悲凉之声。最早的悲秋文字大概要推战国时宋玉的《九辨》了:“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是一幅凛冽的悲秋图,读之令人心寒。中唐诗坛怪杰李贺在《秋来》中描绘的秋夜:“……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坛鬼唱鲍家诗……”,幽深似冥冥之世,这与他仕途失意、抑郁不平的心境不无关系。古人悲秋,常悲国家多战乱,月圆人不圆。“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戎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唐·沈诠期《独不见》)抒发了少妇凄凉独处、临秋思夫、感时伤怀的心情。“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唐.王昌龄《边愁》)则表达了边塞征人思妻之愁苦。悲秋之作,最著名的当推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亭浊酒杯。”风、猿、鸟、树、江、病、鬓、酒共牵一情,同关一愁,可谓悲广愁深。
但同是古人咏秋,由于人的处境、心情、视角的不同,色调也不同。杜牧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诗人眼里,好一派清新明艳、生机勃勃的秋山景色,简直把秋色写成胜似春光了。苏东坡则用“荷尽”、“菊残”看到橙黄桔绿的另一面,安慰友人不要悲秋,写下了千古传咏的名句:“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
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诗词中,毛泽东更以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手法,赋秋以新意,唱出了“战地黄花分外香”、“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的雄伟壮丽诗意,给人以鼓舞,具有使人奋发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