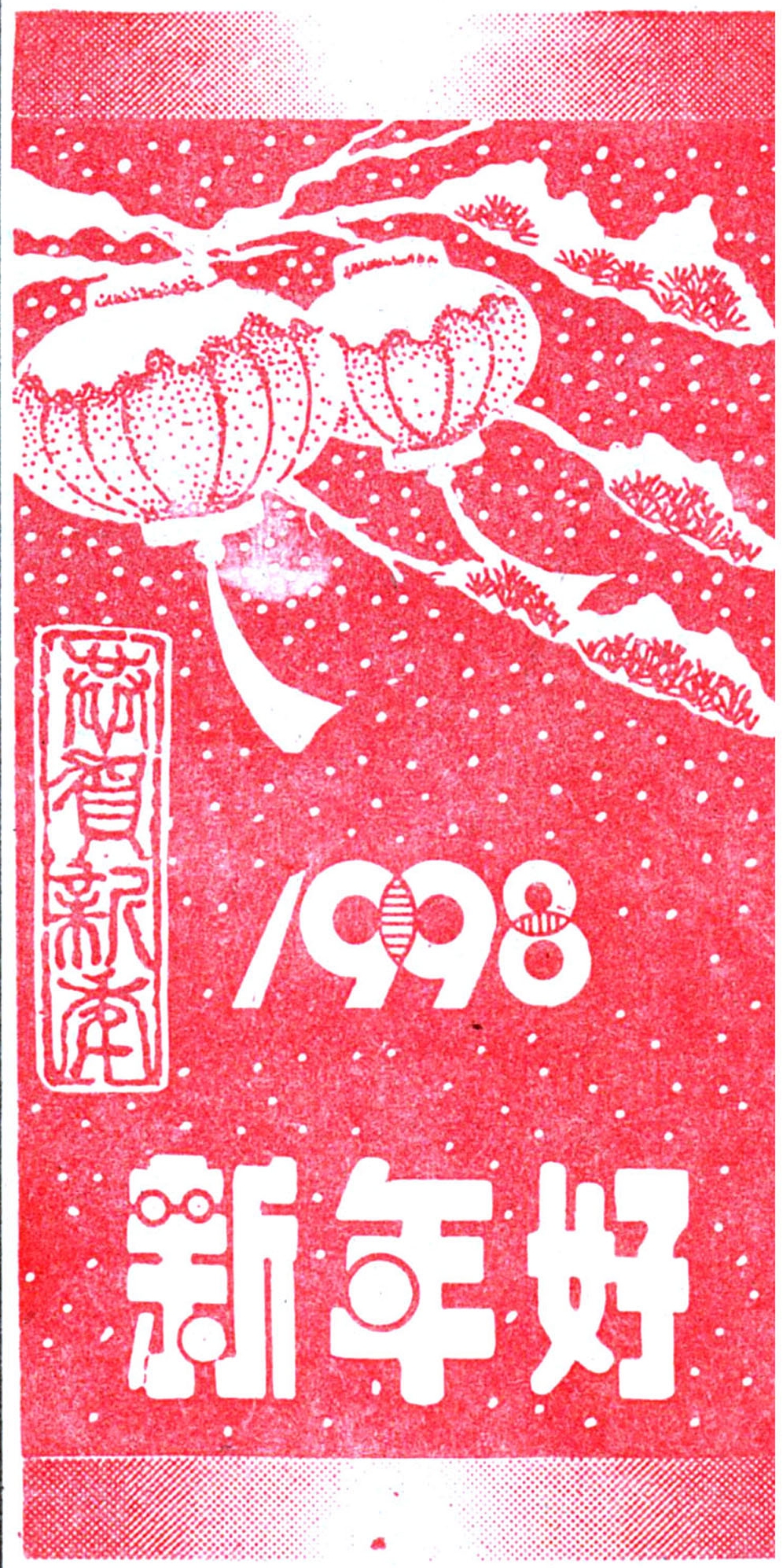文/渭源
每到秋季,总想起红叶。从书籍,传闻中知晓,中国有名的红叶是香山红叶和湘江红叶。渭北塬上有柿树。走入乡下田野,在那缺水少肥的村头田边,沟腰崖畔,老远望去,一颗颗闪烁着桔红色光芒的星体点缀在苍桑的叶丛之中,那便是了。
秋天,柿树的果实和叶子先后由绿变红。叶子尽管不是那样艳红,但也是一团团,一簇簇了。这时,我便经常想起那些出了名的红叶,那些文人墨客吟诵过的红叶。那多指的是枫树、栌树的叶子。我无缘见到它们,但就冲它们被炒得沸沸扬扬就让我生出隔膜。我对柿树情有独钟。柿树也是在季节变换时由绿变红,仅凭风雨中孕育出的那点淡红就使人生出遐想和爱意。何况柿子的果实香甜可口,能带给人许多充实的回忆和启示。
生我的地方是粮食产区,但临县的柿子能用人力车送到我们那儿,即使在交通不发达的前二十年。我们那儿特产少,孩子吃嘴的东西也少。在我小时候,每到秋季能吃上酥软、皮薄、香甜的柿子就算是最大的乐事了。北岸(村上人对渭北一带的泛称)的庄稼人利用农闲季节将自家产的柿子烘熟,一只一只地装上车,拉到我们那儿。有的寄宿在亲戚家,有的找个好心人家作依靠。北岸人缺粮,一般都是用柿子换当地的玉米和辣椒。傍晚,在东家的院子中,用工具把拉上电灯,收工回来的男人便围着柿子摊与卖主谈价,小孩子则在不远的地方尽情撒欢。这时,东家总是偏着外乡人说话,看护摊子。如果价格谈成,大人们便从家里拿来晒干的辣椒,玉米之类的产物,换上半笼柿子,吆喝着自家的孩子,喜滋滋地回家去了。孩子耐不住馋涎,顺手就从父母笼中抓上个塞进嘴里。待到次日清晨,卖柿子的外乡人就拉着换来的物产,赶着牲口踏上了归程,自此,孩子们也把吃完柿子留下的把攒起来当成最好的玩物,小伙伴之间经常比个输赢。有的孩子把赢来的柿把用绳子串起来,足有门框那么长。
听大人们说,北岸人的柿子是用烟熏的。柿子发软,吃起来特别甜。当地人是把生柿子放进温水中,长时间加热去涩,柿子依然是硬的。春节时,奶奶常常把舍不得吃的北岸人的软柿子用开水烫后去皮,和着面,做成饼或条,在油里炸,就成了美味佳肴。对这种每年只有一次的机会我是特别珍惜的。有时,偶然吃上几个北岸人捎来的柿饼,那更成了奢侈的事了。
后来,自己落脚到渭北,时常看到柿树,知道用柿子加工成柿饼,可以治疗咳嗽,咽喉炎等,现在已成为南运赚钱的重要物产了,酿成醋,更是醇正香甜。所以,对它们的偏爱便与日俱增。柿树虽然没有像枫树、栌树那样成为文人墨客吟诵的对象,但它质朴的风韵,却常常打动着我。柿树不趋雅附骚,柿树不争奇斗艳,柿树不挑肥捡瘦,默默的开花,无声的结果,把果和美无偿地送给人类和自然界。难道人不应该学它点什么吗?
我觉得,柿树的红叶才是最好,最时尚的红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