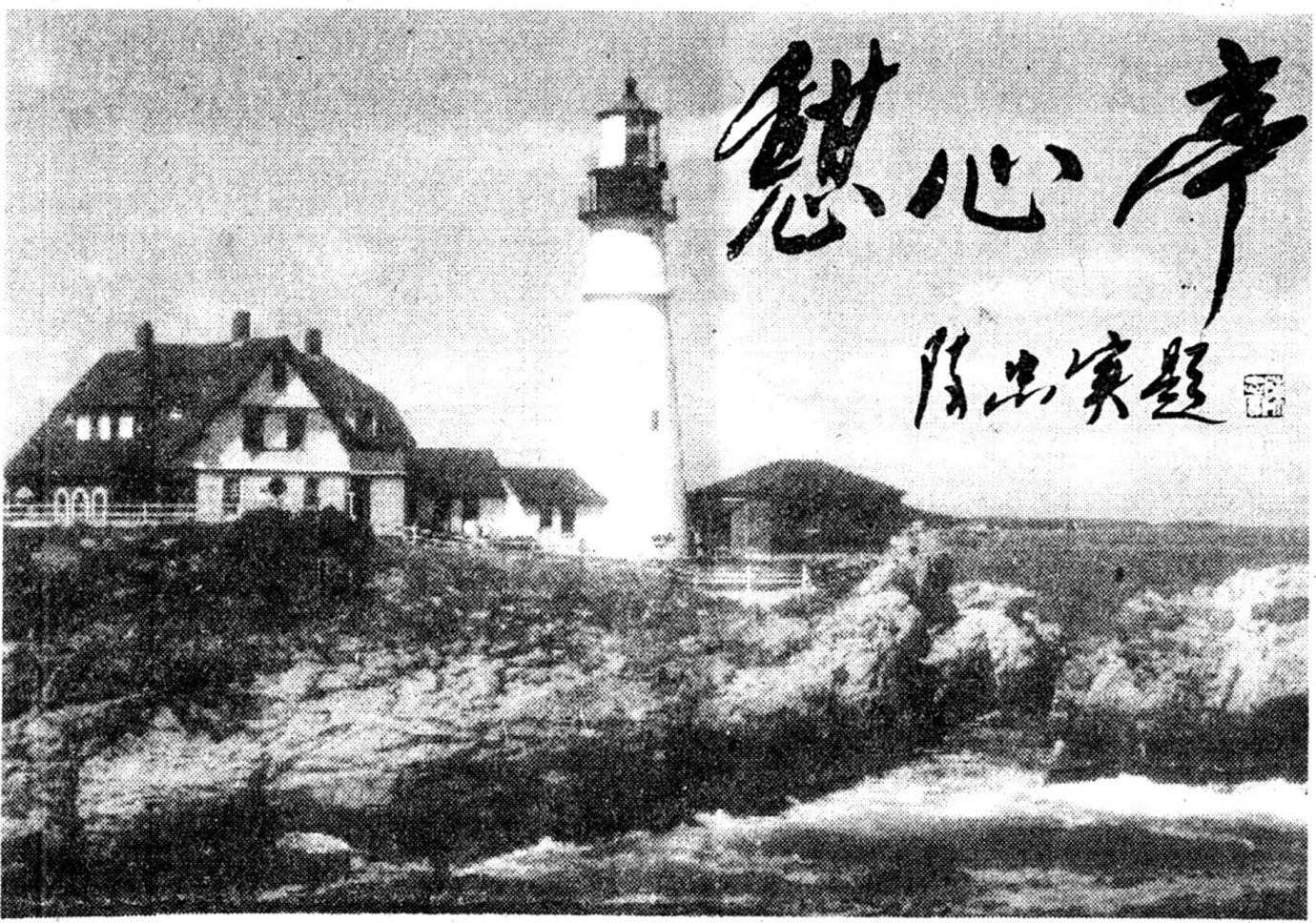文/贾宝泉
散文者,散淡之文也。心放得下,笔才举得起。
散淡为文者,散淡人也。虽云散淡,对于责任和使命,则惟恐持守不力,更无论漠然视之。倘对于责任和使命也漠然视之,那便是心迷一窍。倘忽视艺术品位,同样是心迷一窍。
言为心悟,有话便说,既不教导,也不自显,有信心而不自傲,具觉悟但不张扬。表述可文可白的,宜白;引文可有可无的,宜无;篇幅可长可短的,宜短;做法可繁可简的,宜简。思想则务求深刻。
长有长的难处,短有短的局促。惟其难,才有大匠应运出来,众山里独峙一峰,以补青天之漏。纳须弥于芥子,邀星汉作掌上观,小中见大,此诚乃散文体制所制约,乐于就范此种制约的,大致容易成功;而大中见小,须弥山上寻蚂蚁,往往事倍功半。
学养深到,思索得法,不急功近利,把心从稿酬和奖级中拯救出来——要之,思想便自然、平和、深睿。
质朴平易的作品使人亲近,外柔内刚的作品使人回味,阵马风樯的作品使人动容,色厉内荏的作品使人隔膜,高高在上的作品使人腻烦。作家无论如何改良汉字和章节的拼接方法,甚至在汉字的音韵上下忒多的工夫,只要读者不亲近,有隔膜,便不读或少读。出新、出奇都是必要的,然而说到底,句子新,诚不若文意深也,舌粲莲,终不如根拒污也。中国是举世公认的散文大国,不事写作而深谙散文三昧者,多若恒河沙数。这些不顶冠冕的评论家,虽然较少知道文学艺术新术语,但对于作品的批评,往往比专职评论家更少利害关涉,因而可能更关痛痒,更公平,更透彻。作品优劣,最终还是他们说了算,历史喜欢听取这些人的闲聊,却爱开职业专门家的玩笑。同作家相比,他们是稳坐钓鱼船的最后的赢家。
历史确认作家层次从来都是不慌不忙的,甚至是懒洋洋的,作家自己却等不及。
金刚怒目,菩萨低眉,霹雳挟雨,杨柳含烟……散文之千千面,亦作家之千千面也。
散文的垅亩原无边际,好心人却为之辛勤设置篱笆。不过,虽有篱笆,仍有人视为整块田园,逍遥于风流蜃动,云卷云舒,总题目就是中国散文派。如果在散文的垅亩内打量人生略嫌束缚,那就移步于散文之外,在文学圈子之外揣度人生、感悟文学,可能会比较冷静、自在、确当。同文学圈子若即若离,有时候同样是良好创作心态。窗外的世界,一般要比窗内的世界大。人不甘心囿于小世界,才向大世界借景,甚至执迷到去冰天雪地的旷野上露营,夜半冻醒便以唾润唇,走笔荒寒之境,静候朝暾从天而降,大不了招惹一场重感冒,反正墙壁是向前后左右无限推远了。
一件作品写得好不好,往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标准不一而足。男作家的作品可以放
心地给女儿看,女作家的作品可以放心地给儿子看,儿女欣赏品味时作家不慌张,这,也是标准。前辈从哲学因果律推出大含细人的两句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究极了看,今天和昨天、明天是同一天,现实和过去、未来是同一阶段。如果不对今天承担责任,不在今天种下善因,也不会有摇曳着沉甸甸的禾穗的明天。没有明天,也就无所谓昨天了。
圣哲云:“大道至简至易。”散文的秘密,说多也多,说少也少,概而言之,窃以为就只有“会想、会说”四个字。这四个字,百万字未必说得清楚,几句话过后也许再无话可说。这就看说话者如何说、听话者如何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