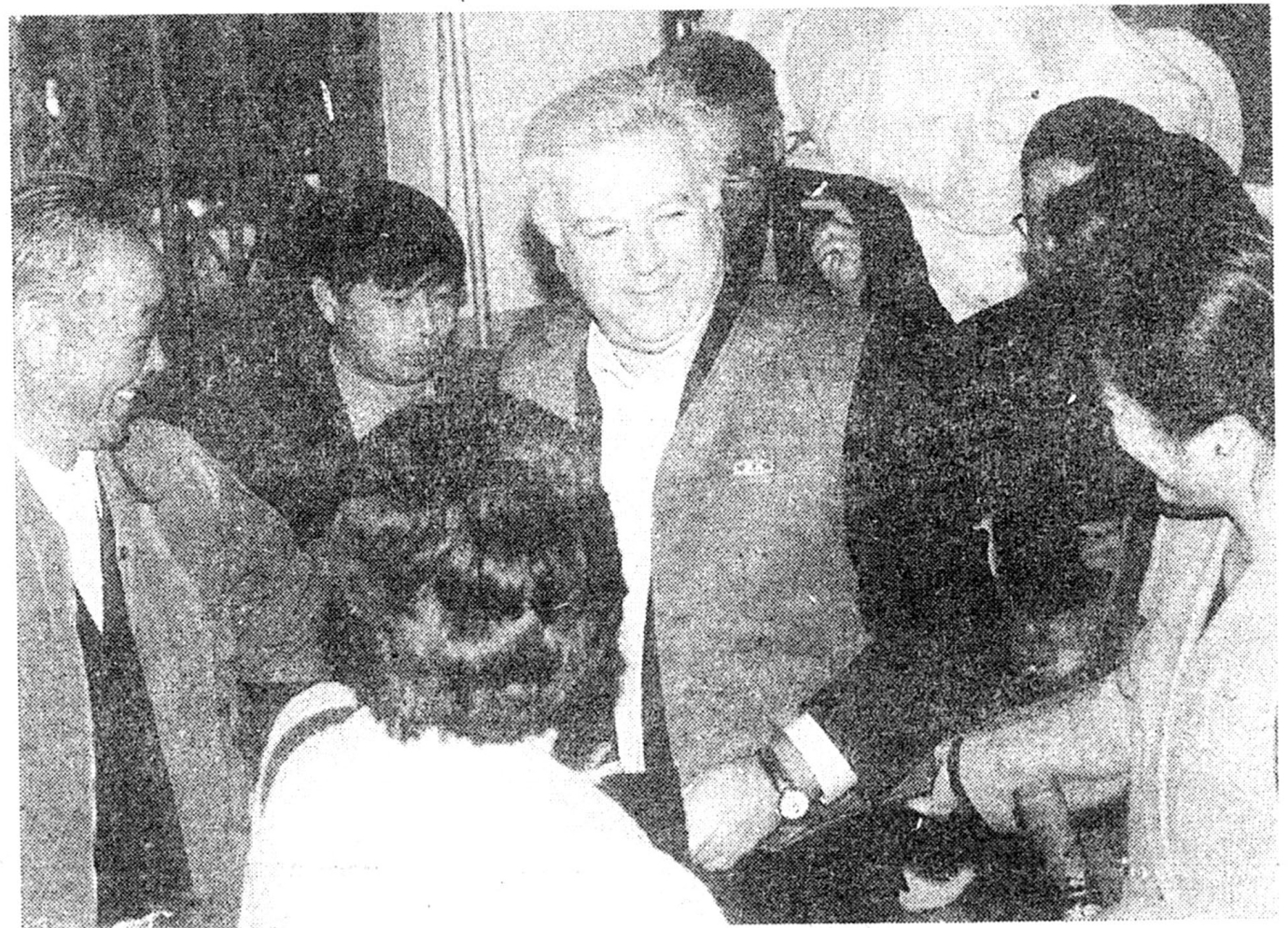见了陈宝生你会失望,你无法把文弱的他和那些气吞山河的“跃马”相联系,你很难相信,就是这样一个人,能光着脚丫子一步步从陕北的黄土窝窝走向世界,有多少头衔不说,在国内获多少大奖不道,单国际大奖他竟获得102项,真算得上地道的国内之最了。
他确实创造了奇迹,他使整个世界吃惊,台湾省定评他为:“中国当代的徐悲鸿,摄影界的画家,暗室里的魔术师,海市蜃楼的雕塑家,独一无二的摄影建筑师。”欧州人誉他:“东南亚的马王”并道:“上下近百年,左右千万里,没有一个人在摄马领域和陈宝生匹敌!”
陈宝生的成功再次向人们重复一个简单的道理,艺术的大成就要靠诚实,要赖一生的苦,要不惜用生命作赌。
用15年寻找马的龙性
1969年秋,在我省定边县和内蒙古交界处,陈宝生去拍马。天刚下过雨,草地积一尺多深的水,他的交通工具是一匹枣红色的马。马很温顺,第一天顺溜溜地骑了60里。第二天一大早,他便进入马群开始工作,机子刚一打开,随着朝阳在镜头上的折光,突然,马长啸一声,四蹄腾空,狂奔而去。陈宝生大惊,急扯住缰绳。见状,牧民大喊:“缰绳勒紧!”他越勒马越跑得快。两牧民急忙策马追赶,10里之外,牧民才一左一右把狂马夹拉住。马已浑身是水,满口流血。陈宝生一下子瘫在地,惊魂略定,便不解地道:“昨天还温顺得很,今天咋成了这个样子。”一个牧民告诉他,“这就叫是马三分龙。”陈宝生大悟,从此,开始寻找捕捉马的龙性,这一找就是15年。
险被“龙”踩成泥浆
1972年,陈宝生构思了一个作品,叫“排山倒海”,选用军马,共150匹,角度为正面。起先的计划是,选一个低洼处,在群马跑至10米处启动快门,然后躲开。但实际和所想距离甚远。连长马刀一挥,百马狂奔,10米处快门一按,那里有躲的机会,还不等他眨眼,马已跑在头上,他急忙抱了头爬在地上,等150匹马过完,马蹄腾起的沙子把陈宝生都掩埋了,赶连长把他扒挖出来,陈宝生已是气息奄奄,看陈换过气来,连长便冲着他喊:“险些出大乱子,你也真会开玩笑,你不要命我还要命啊!”
这幅作品获英国皇家摄影俱乐部银牌奖。这是生命的代价。一胎三年
陈宝生的暗房墙上贴有一个座右铭,即“功深百练”。国内外传统的摄影有焦点透视,即由近至远、至消逝点,一张照片一个透视点。而陈宝生则相反,他追求的是“散点透视”,即多点透视,一张照片由众多的透视点组成,这是陈宝生的杀手锏、秘密武器。这也是陈宝生的摄影特点和风格。陈宝生艺术上的创新如此,在作品立意上所用的功夫更是惊人的,他有“三年怀一胎”之称。1983年,米脂印斗乡有一个交粮专业户,叫姬壮银,两年给国家交粮1.6万余斤。过去极穷,现在勤劳致富。陈宝生住在其家,想拍张照片。姬壮银每天招待陈宝生的菜总是5碗肉,陈不解,姬解释说,“这叫五魁。”又说:“现在的农民才叫真翻身,前年正月初一,全家吃了一顿饺子,初二就开始吃豆渣馍馍,现在我们天天可以吃五魁。”他极得意,接着又说:“我满足了,我什么也不想了,每年收入一万多元,一家4口,生活得就够幸福了!”看了姬壮银的得意,陈宝生便确定了一个主题,他要用照片反映党的致富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幸福,又要批判农民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思想,即自傲、自信、自我陶醉、自我满足的思想。但一连三天,陈宝生找不见反映这种思想的画面,不得不无获而归。
1986年(3年之后),在神木尔林兔乡,又碰到一个和姬壮银同类型的人,他叫曹志悍,是个牧民,养一百多只羊,一年收入一万多元,陈宝生在面阳的山坡上采访他,曹怡然自得,谈高兴了,便唱:“33棵荞麦99道塄,阳洼里的糜子背洼里的谷。”唱罢又吼:“我老汉知足了!”接着半躺了,夹一口烟,咪了眼的乐,头顶一排卷着角的大绵羊也咩咩地伴着主人的高兴乱叫,陈宝生眼睛一亮,立即按下快门,这幅作品的题目叫“黄土魂”,在国际上获得8项大奖。这真是不生则已,一生就是个金蛋蛋。 (翟龙 王津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