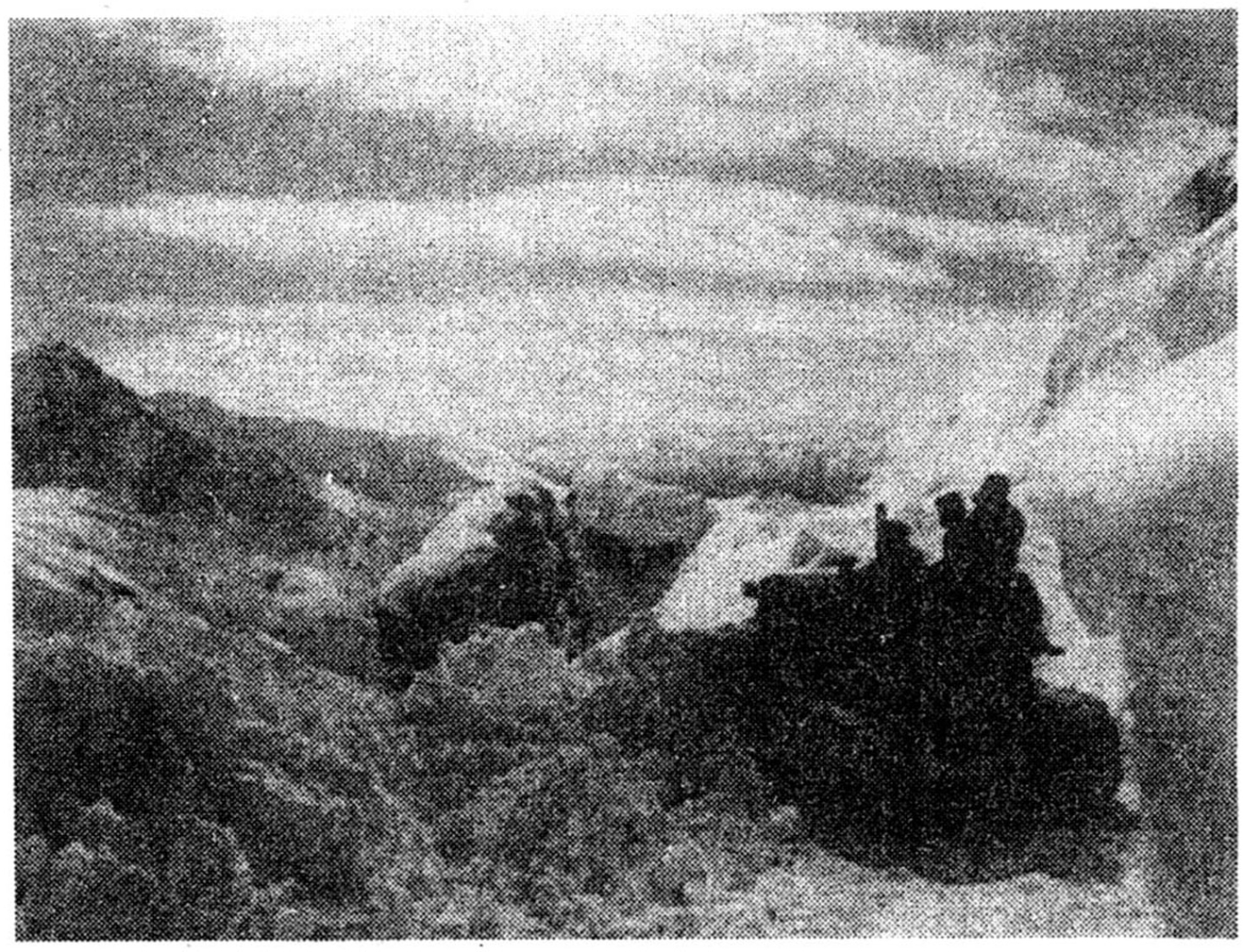文/杨帆
力图通过立法将部门利益合法化。行政权力对于法制的干扰,在执法方面主要是地方保护主义。而在立法方面则主要是部门保护主义,我国立法任务极为繁重,人大立法往往通过行政主管部门起草,正式法律往往需要大量行政法规加以具体化,因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借机将部门经济利益塞入法律和法规。
使用各种手段维持部门垄断,反对市场准入。某些部门以“整顿秩序,加强管理,保护民族工业”为名义在外贸、批发商业、邮电、金融保险、建筑等行业,规定严格的市场准入措施,限制非国有企业和“非嫡系部队”进入本行业自由经营;在国土管理、外贸许可证管理、户籍管理、原始股票发行、贷款指标等许多方面,不采取市场经济的公开拍卖方法,而长期维持内部审批、小范围招标、行政分配。
采取新的方式维持“官商一体”。中央虽然三令五申:行政主管部门与自己所属的公司脱钩。实际上不彻底的脱钩,反而成为更隐蔽的挂钩方法:行政主管部门和某些有特殊权力的部门,利用自己的权力申请许多难以批准的经营权甚至是特许经营权,办金融,办通讯,搞房地产,经营“高档娱乐”,如桑拿、按摩之类,经营防暴器材甚至武器等等;主管部门利用权力疏通关系,购买廉价地皮,争取优惠贷款,获得计划指标和许可证,抗拒检查,以保证公司获得超额利润,自己坐收红利。这种表面上脱钩比公开挂钩更为恶劣,是因为经营者对主管部门一级组织来说,有了独立性,同时与个别权力人物的关系则更加紧密,更加具有谋私利的性质。而主管部门对于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可以公开以“已经脱钩”为理由不负责任,转而采取私下包庇的办法。
公开“设租”,高额收费。经济学上有所谓“寻租”之说,是指社会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影响议会立法和政府政策,以获得特殊利益,随着我国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利益集团为主体的寻租活动必定日益严重和公开化,同时以管理部门为主体开始“设租”:直接扩大管理权力,出卖部门掌握的稀有资源,以牟取暴利。
行业腐败日益扩大。所谓“行业不正之风”,已经超过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和单位之间小额利益交换的界限,发展到由主管部门有意支持纵容甚至出面组织和制造的“系统化腐败”,教育腐败、科研腐败、干部选拔腐败、有偿新闻等。在紧缺资源背后,我们总可以看到高价黑市,如高价卧铺票、演出票、专家门诊号等等,如果没有内外勾结,如何倒卖?
协助企业向政府“寻租”。行政主管部门,在计划经济下,是各级政府的下设职能部门,直接组织各行业的经济活动,其宏观管理职能和国有企业所有者的职能是合一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在法律上已经分开,所有者职能划归国有资产管理局。但是主管部门仍然抓住其下属国有企业的经营权特别是组织任命权不放,在政策实施上偏向自己的“嫡系部队”;同时,帮助更多的非国有企业向政府寻找优惠政策,主管部门的一些干部则私下充当他们的“经纪人”,获得巨大好处。由于与企业接触过多,利益结合过于紧密,所谓“主管部门”,一方面以“加强管理”为名发布无数管理条例,一方面私下里协助企业“绕道而行”,以获得额外利益,某些主管部门与其说是宏观管理部门,不如说是一个企业总部!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