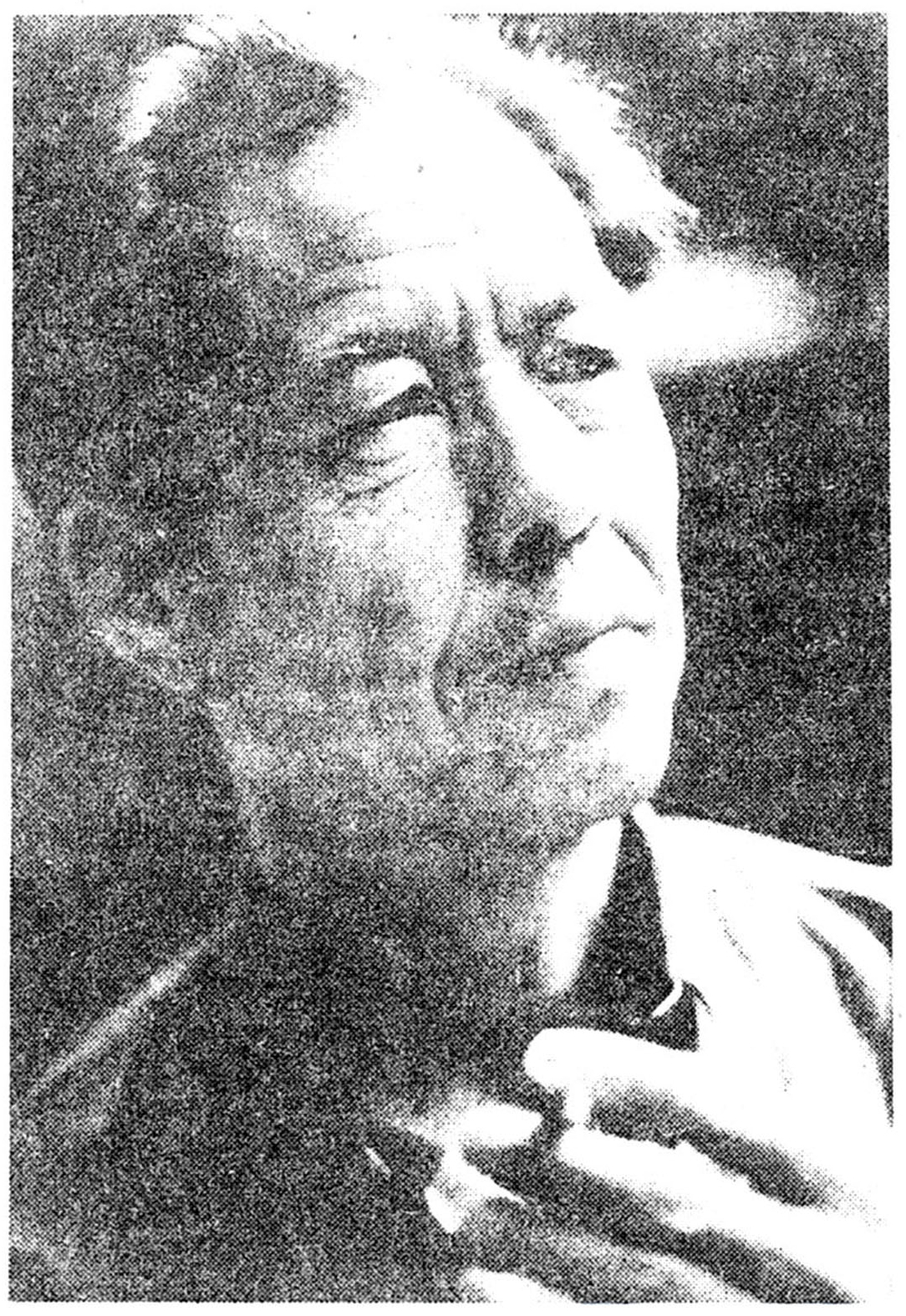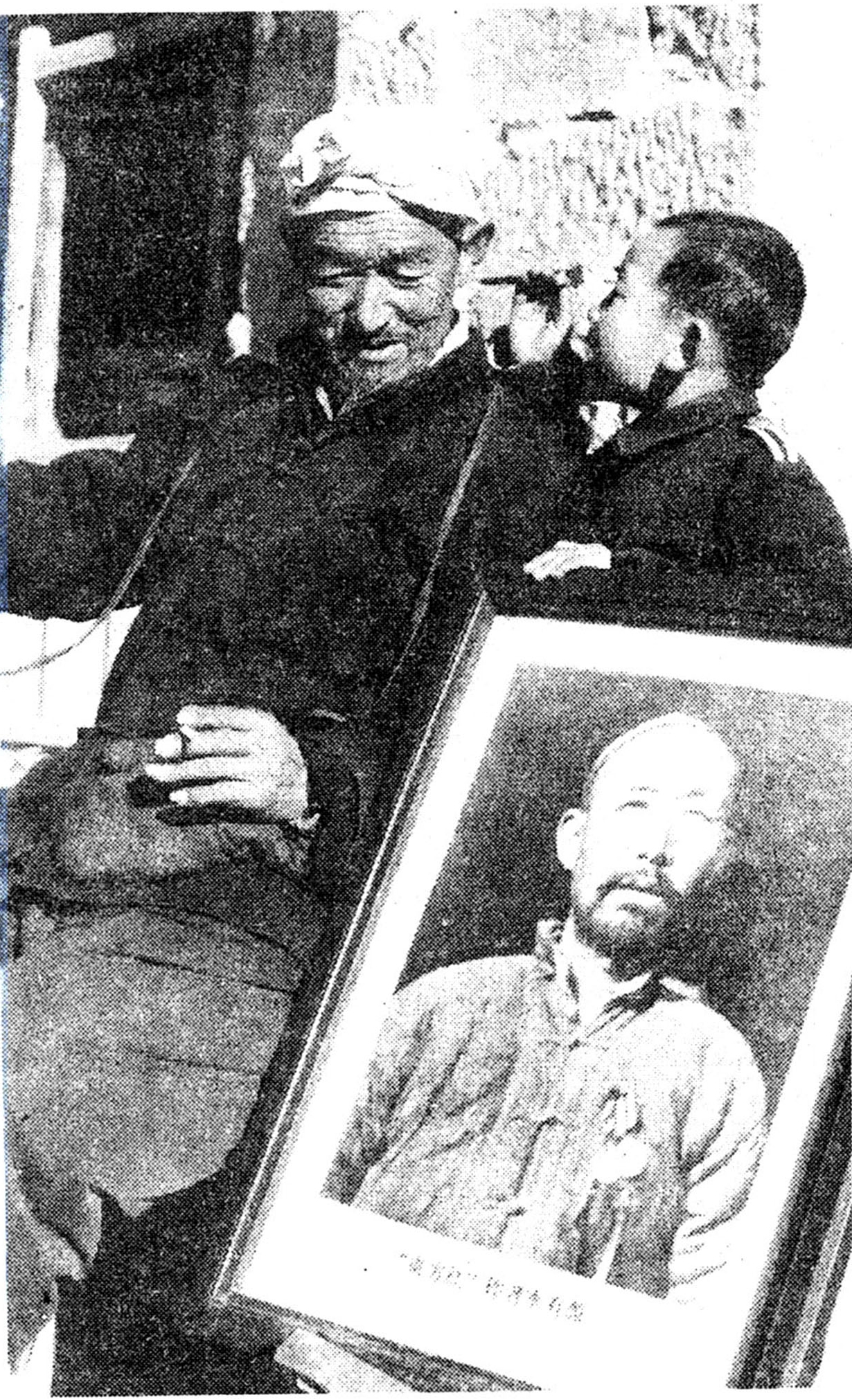文/梁萌
当《白鹿原》在西安发行的当天下午,陈忠实托人给我送来一本他亲笔题赠的《白鹿原》后,我匆匆地吃了几口晚饭,便躲在书房里看开了。连着看了两个通宵,我终于看完了这部长篇巨著。当我掩卷沉思,冒出来的第一个感觉是,他必将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而且也必将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那样获大奖。此后我一直在企盼着这个消息,不料,几年过去了,不仅没有盼到,而且还传出了另外一些说法……然而,正像在省作协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祝贺会上,评论家王仲生、王愚等人所说的那样:时间是文学最公正的法官,一部作品是好是劣,不在一时的喧嚣和炒作,也不管怎样抹杀,而在于作品本身,时间越长,就越能显示出他的真正价值,“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才是真正不朽的作品!”
事实不正是这样吗?翻开中国文学史,不要说有争议的小说,就是世人公认的名著如《红楼梦》等,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不是也被一些人视为“淫书”、“邪书”甚至被禁读吗?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真正价值和历史地位才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所接受,直至成为不朽!
这里,我不想就《白鹿原》的成就和她的历史地位再作赘言,因为有好多专家已对此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只想就陈忠实作为一名成熟的作家显示出的“沉静的心态”说几句。我们不妨先看看《白鹿原》获奖后,一家市级报纸刊登的一篇“评说”中的一段话:
(当《白鹿原》获奖的)消息传来,有人问陈忠实:“您对这次得奖是否感到惊喜?”他一如平常般心平气静地回答:“不感到吃惊。”他解释说:不感到吃惊并不意味着这次得奖是我意料中的事,或者说事先我就自信《白鹿原》一定能够获奖。而是因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应该有成熟的沉静的心态,得奖与否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记住:历史淹没的必然是那些平庸之作。当初创作《白鹿原》时我的心态是沉静的,如今,我的心态仍然是沉静的……
多么难得的“沉静的心态”啊!由于受外来诸多因素的影响,近年来,许多人特别是文化艺术界的一些人已经把“人怕出名猪怕壮”的传统观念抛到九霄云外了,追名逐利在一些人那里不仅已不再是贬词,而且成了拼命争夺的“目标”。比如有人只拍了一两部片子,便急着要出名,甚至不惜花钱雇人为自己炒作、吹嘘;有人为生活丑事吵吵闹闹,唯恐家丑不外扬;有人声称削发为尼,制造轰动效应……纷纷扬扬,浮躁虚伪,这与陈忠实“沉静心态”的对比是何等的鲜明!
陈忠实的这种“沉静心态”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平常心”。说到“平常”,我不由想起了去年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谜语故事——这篇文章的作者刚参加工作时,一位同事给他出了个谜语:道士怀揣两块糖,和尚足下一条巾——打两个汉字。作者七猜八猜,好一阵子,还是没猜着。后来同事给他说穿谜底:“平常”。“你看嘛”,同事得意地向他解释:“道士”是谐音,实为“倒士”;而和尚的“和”字在此处具有“连词”的意思。原来谜底就在谜面上!道破了其中的玄妙,就这么简单,可看不破,就这么难,陷在那个“圈子”里七扭八扭也走不出来!
陈忠实所以能在浮躁的氛围中保持“沉静的心态”,除了因为他早已看透了这种噱头热闹,只能喧嚣一时,而难得长久,正象他所说的那样:“历史淹没的必然是那些平庸之作。”还因为他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所具备的那种素质。正是因了这种素质,这种“沉静的心态”,陈忠实在白鹿原这个远离城市喧闹的地方,整整熬了七年时间;也正是因了这种素质,这种“沉静的心态”,陈忠实摆脱了当时那股几成时尚的文人“下海潮”的影响,一心一意呆在那间房子里,苦苦思索,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最后终于铸成了这部被誉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高峰的巨著。
作品是这样,作人又何尝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