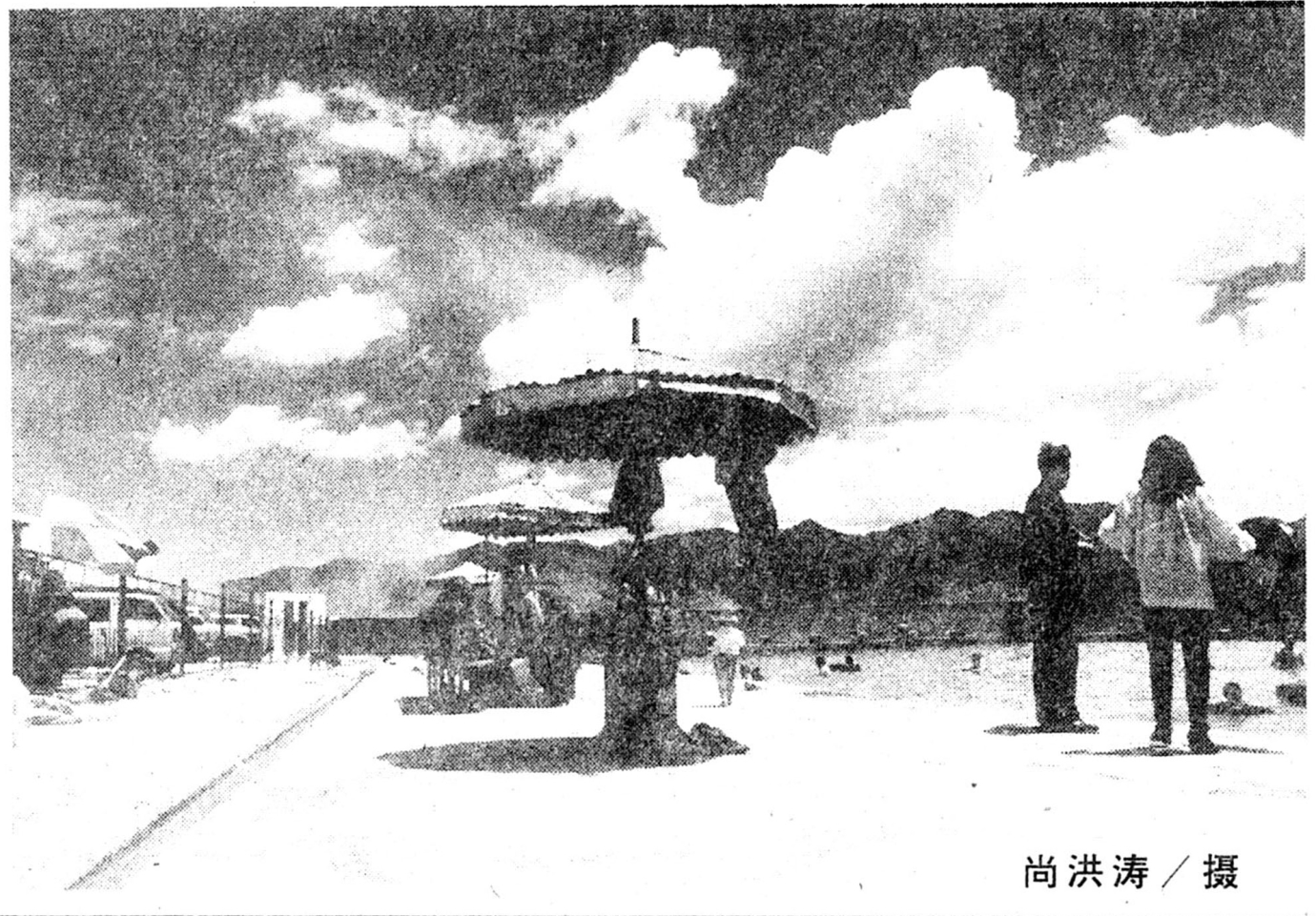文/李春燕
相隔万水千山,那里住着牵挂我、思念我的亲人。
每天城市里那座古老的大钟、、地敲响,大地还在梦中,即将被隐退的弯弯的月牙还白白地挂在树梢上。悠扬、浑厚的钟声飘进曲折的巷子里,靠第三根电线杆二楼窗棂的灯亮了。一位老人,拎着两个水桶,趔趄走出仄仄的小楼梯,“咯吱”一声打开大门。因为天还没亮,公共水管上则不需要排队。老人将注满水的水桶吃力地提起,重量压在她的前心后背,使她本来弯曲的腰身更加萎缩了。老人深一脚、浅一脚地从第三根电线杆到公共水管要走几个来回,直到大缸里被注满了水。然后又提起一大桶污水朝一个相反的方向走十几米远,在一个公共厕所里倒掉。天亮了,可以看见起伏跌宕、挤挤攘攘的房顶上挂着的冰溜子。护围的钢筋上的锈粉参和着残雪被凝成片。水泥地的地板和墙面十分粗糙。玻璃窗十分简陋,为了抵御寒风,在接缝外全部用纸条糊着。老人站在二楼四面临风的过道里,守着一个炉子,沾满油和面的手在油锅里翻飞,她已经烙好一叠饼。风,更紧了,呜呜地叫响,像刀子一样刮在老人的脸上。她的棉袄外罩被风揪起一襟,露出蓝银银的袄面,她的头发在寒风中缕缕散开,象划破的白云。
老人将烙好的饼放进一个铝锅里,又塞进一把葱和一碟面浆,另一个篮子里是一锅小米稀饭。老人锁好门,又一次走那窄窄的楼梯,两只篮子不时地在她腿上磕磕绊绊。
这位老人就是我的婆婆,她是给在复印部工作的公公、爱人和兄长送饭去了。
正当一家人嚼着煎饼,喝着稀饭的时候,婆婆已经开始了她一天的工作。
婆婆脚宽,她从来不穿皮鞋,嫌挤脚。正是这双宽大肥脚,使已足65岁的婆婆身轻如燕。婆婆不会骑车子,又舍不得花钱打的,在来到这个城市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为了找一间门面房,她走遍了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夏天,脚下似火开腾,婆婆汗水直躺,却舍不得买一瓶汽水喝。房东见婆婆是个外地人,又上了年纪,就连懵带唬地说:少了三万不租。婆婆租下那间门面房,每个月除去房租,生意还不错,那是婆婆和公公起早贪黑干出来的。
中午,婆婆从外面赶回来,要做七八个人的饭。婆婆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所具有的秉性,女强人做不到,她是一个比女强人还要“强”,比家庭妇女还要“家庭”的人。
转眼就到了夏天,早就传说那古老而又陈旧的巷子要拆,从春传到夏,又从夏传到冬。那年夏天真的开始拆了。拆房子就像是一枚定时炸旦,悬在婆婆的心中。婆婆是外来人,在这座城市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蔽身之地,要拆了,为了再重找一间住房,婆婆几乎跑断了两条腿。晚上躺在床上,听着从拆迁指挥部飘进来的“高音喇叭”和“空空”铁捶挥舞的声音,嗅着石墙破裂后的土粉味和陈霉味,婆婆心急如焚。眼看就快拆到第三根电线杆了,婆婆还是没找到新的住处。
在我的家人只抢出一张床,一些衣被和部分炊具的时候,铿锵有力的铁捶,实实地在婆婆住过的房子上“开凿”了,只听“轰”的一声,房子倒了,而我的婆婆抱着从房里抢出的最后一床被子冲出来了。她的双脚被废墟湮埋。
最后婆婆搬到了一个六层楼上。房主吸毒,他把家里所有值钱东西都卖了,最后只好出卖他们唯一的、仅有的栖身之地。腾出一间给婆婆住,两家各上一把明锁。
住这样人家的房子是极不安全的。婆婆是个明细人,可她实在没有办法,至少住在这,要比流落街头强。婆婆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房主被戒毒所抓走,又被释放回来后的第二天,婆婆住的那间房门被撬开了。幸亏没有损失什么,那间租用的房子里,除了破烂还是破烂。
婆婆面无声息地换了把锁,却整日提心吊胆。她把放在两家过道中间的水缸和做饭用的炉子,全部提进屋里,怕被人投毒。那间被堆积成杂货铺的小屋,象个锅炉房,在炎热的夏季,整日热气腾腾。婆婆身上长满了痱子。
第三根电线杆,早已是一片瓦碎和砾石。婆婆站在她曾经住过的那块空地上,碎石硌着她的脚心,她心中所企盼的属于她自己的房子,何年?何月?才能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