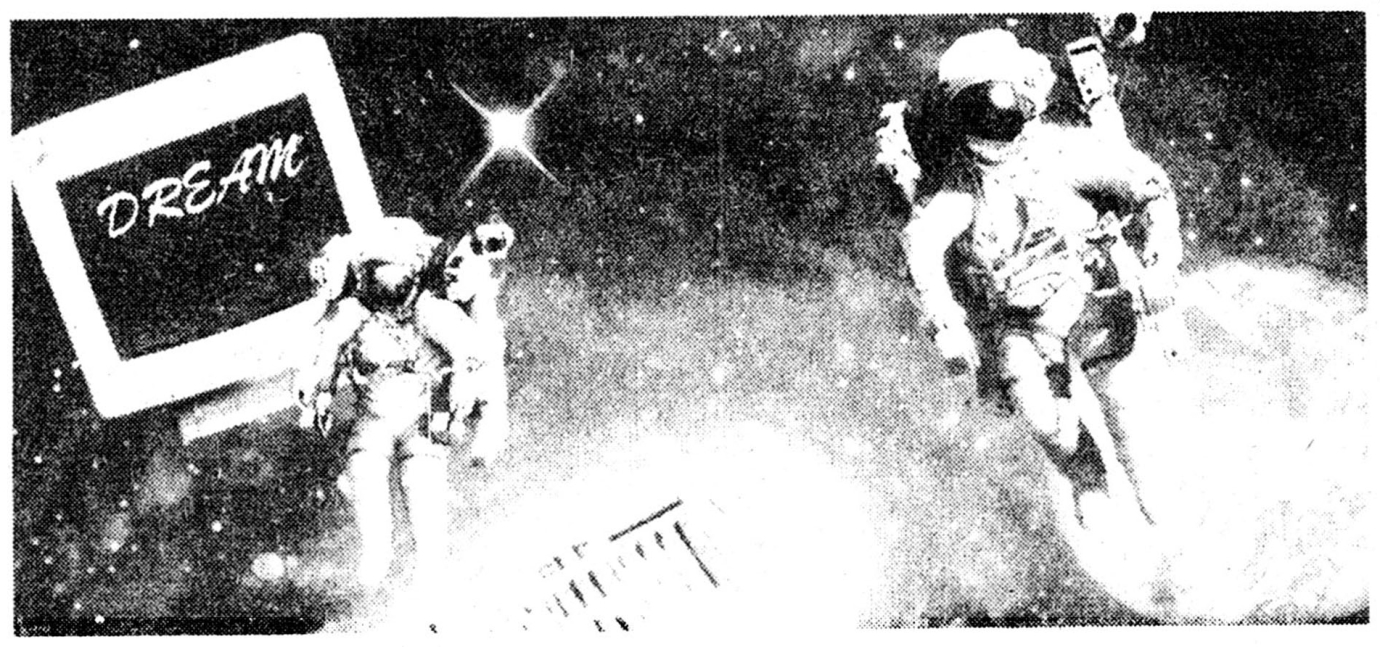文/田保荣
中国人喜爱菊花,因为此花有不畏寒冷和恶劣环境的傲骨,代表一种不畏强暴的精神,但法国人对其并不像中国人那么热爱。倒是相反,我多次给法国人讲中国人爱菊花的道理,而且讲得很费口舌,法国人似乎总是若明若暗,似乎菊花不畏寒冷,傲然怒放并没什么特别值得欣赏的。反过来,我对他们的这种木然态度也一直大惑不解。
因为不解,总免不了要去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我们看来那么可贵的东西,他们竟无所谓。中国人总把菊花和傲然挺立,直言敢谏,不趋炎附势联系在一起,可就是这些,法国人不理解,他们不以为然。至此,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物以稀为贵,自古如此,中外亦如此。中国人之喜爱菊花,正是因为菊花精神之匮乏,法国人对此不以为然,大概因为敢说话在法国根本不算什么,就像喝一杯水那么平常。不是么,法国电视一台、二台、四台都有政界人物漫画式木偶对话表演,每天在20点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前播出,由各台的专门人才将当天政界发生的事集中概括成几句话,几个动作,然后模仿政要们的声音演播。这个节目大概算是很开心的。例如1993年议会选举结果,右派获胜,人们都嚷嚷说密特朗总统只有辞职了,《串鸭报》甚至有副漫画,希拉克给密特朗指门,嘴里还说:“门在那儿。”法国人的习惯,指着门给对方说这话的意思,就是令其滚蛋。按中国的传统,搞这个节目的那几个人肯定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了,可是法国就没有这一说,敢批评国家和政府首脑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且不需要冒任何险,比指责街上一个行人还安全,因为该行人可能会和你干起来。总统、总理、部长及各党派党魁则不会。如果这些大人物中有人给指责过他的人穿小鞋,各报刊电台、电视台记者可就有话说了。所以即使想整人,也不敢下手。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总统刚发表完新年祝词,或刚举行完记者招待会,紧接着就是各方评论员的评论,真是评头品足,有的说总统在这个问题上耍了花招,有的说在另一个问题上推脱责任,文过饰非,毫无新意……等等都可能用上去。
说起花儿来,我真为我们喜爱的荷花叫屈,因为它在法国境况很不好。为中国人之喜爱荷花,我也费了很多口舌,因为我教的太极拳里有个动作叫“摆莲”,而法国人在这里偏偏困难很大,有的甚至问为什么要把这个动作叫“摆莲”。我则告诉他们中国人对莲花,即荷花的偏爱,讲此花出污泥而不沾,洁身自好。法国人始终像听天书,他们认为,任何秧苗从土里或泥里出来都不沾泥土,荷花和别的植物一样,所以很不以为然。正由于这样个差异,法国一家企业生产的手纸的牌子就是“荷花”大概是因为纸的颜色像荷花花瓣。我每看到该手纸的广告总有点气愤,总在想,这么高雅的东西怎么可以拿来做手纸的牌子呢?但又想,这也是生存条件而异的原因。中国人和法国人拥有共同的太阳,但仍有点差异,例如法国就没有类似我们“夸父追日”的神话。何以如此?大概是因为法国人历史上的黑夜没有中国的可怕。由此而想开去,也大概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出污泥而沾污泥的居多,才显得出污泥而不沾的精神的可贵,故而引为崇高。我不是历史学家,不敢肯定这一说法,但可以引出我脑子里的一点存货从旁证明我的这一说法有些根据。我们有句谚语说,“久在河边站,怎能不湿鞋”;还有一句成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历史我不敢枉谈,但现实我可是看见的不少。有些国人爱占公家的便宜,是人所共知的,办公纸、笔、墨水、胶水,甚至连办公室的拖把都扛回家去的也是屡见不鲜的。法国人绝少有此种行为,甚至办私事也绝少用公家的电话。我说不出这个差异的原因,估计跟受的教育有关系,也和经济基础有关系。中国人的智慧是法国人叹服的,我们的祖先早就总结说,饥寒生盗贼,此话差不多是真理。因为普遍的贫困,就使得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下降,再加上道德教育的畸形,人的行为就很难检点,于是出污泥而不沾才显得可贵、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