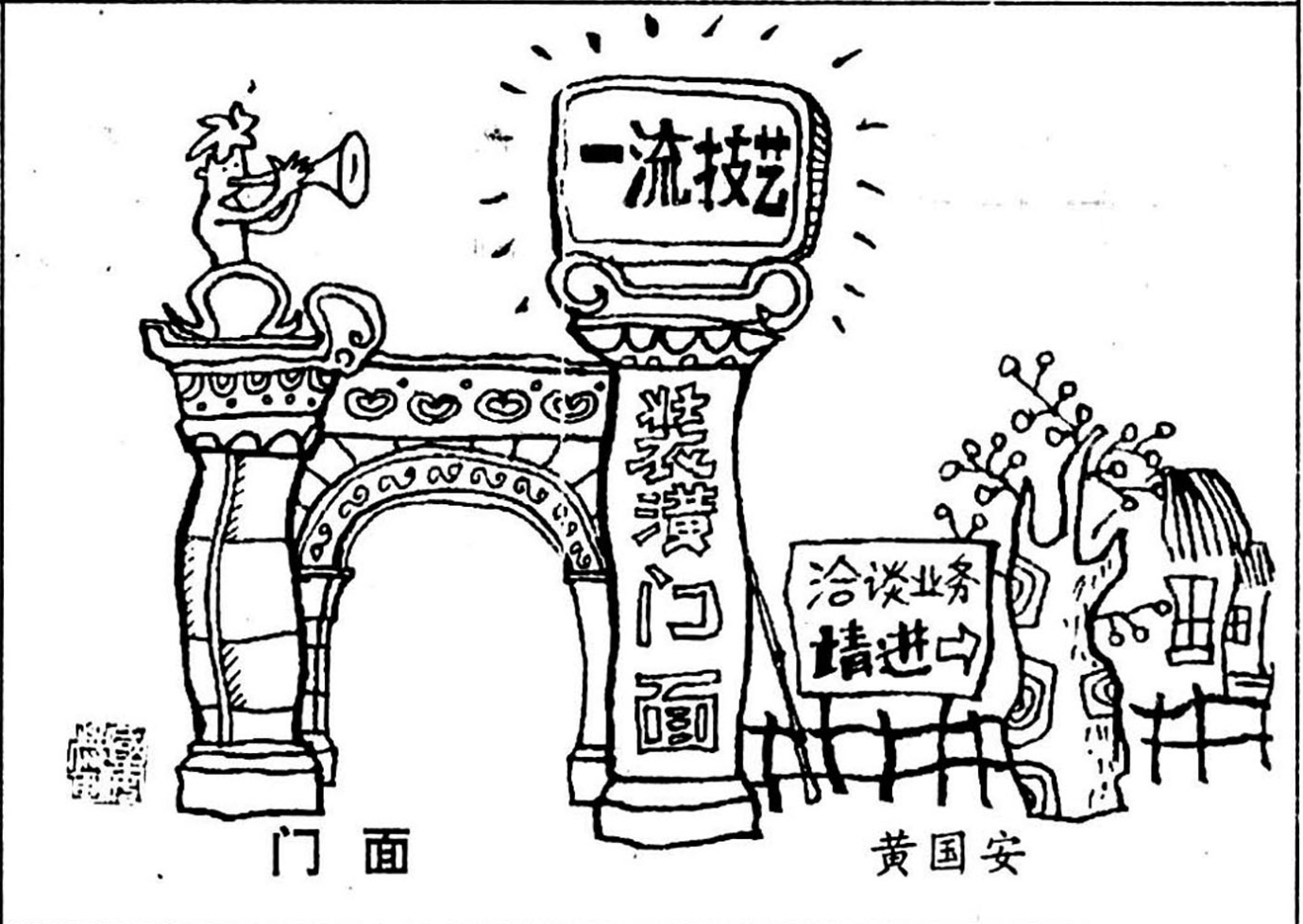燕川
长期以来,“免予起诉”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即不经过人民法院,而由人民检察院单独作出一种“带罪处分”:认定被告人(嫌疑人)犯有某罪,但较轻微或因其他原因(其实往往包含关系网、领导意志等影响),不限制其人身自由,不对其提起诉讼,只是宣布对其“免予起诉”,即告本案刑事诉讼结束。这是我国独创的。但是,修订后的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已取消了“免予起诉”这种特殊的“带结果”的刑事诉讼手段。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士指出,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取消免予起诉,“是把原本符合免予起诉的,纳入了不起诉的对象”,“这正是赋予检察机关修正案件的一个权力,也是对案件的裁量权”。
在刑事诉讼中,“不起诉”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现在多数法律学者赞同三分法: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不起诉。免予起诉归入不起诉应属于后两种情况。把它归入不起诉符合我国社会法制现状,也符合国际通用的“从轻原则”,符合我国倡导已久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免诉到底算不算追究了刑事责任?在“处分的依据”、“犯罪与否”等概念上容易造成混乱或模糊。其副作用还在于:把一些可定罪可不定罪的、证据不足待查的等(如同案主犯在逃,待查),统统简单化地“戴上有罪的帽子”,再结束对其的指控——免诉,使代表国家实施审判职能的人民法院无法管辖其中可定罪的和可判“免予刑事处分”的一类案件。这就不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另外,有些罪行严重、只是部分未查清的被告人也往往因不正之风、关系网帮忙,钻了法律的空子,受到免诉处理。从实践看,一些犯有轻罪的不务正业者,免诉对他们无足轻重,震慑力不大。个别执法者为使自己较差的办案质量不受监督,就给别人(“有错而无罪者”或者“无辜者”)强加“免诉”,自己好下台阶。
因此,纵观多年实行免诉的情况,取消免诉是完全必要的,它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有助于提高检察机关办案质量,其综合社会效益将在实践中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