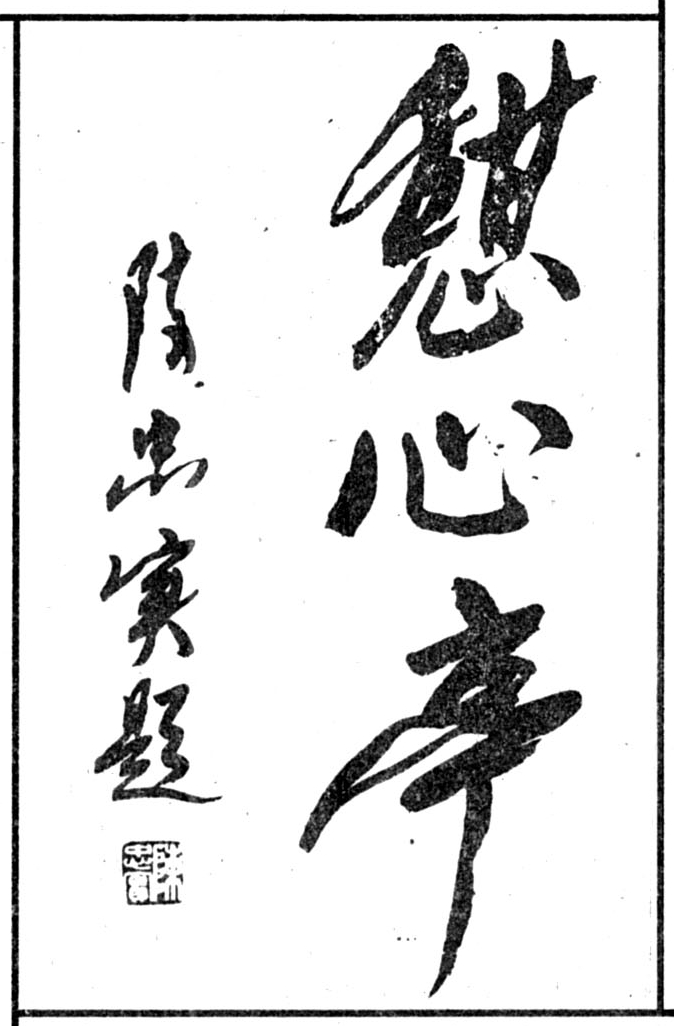文/毛越
顺着知青点楼房后面的一条斜坡路,我们走上了骆驼岭。与往常不同的是,这天岭上风特别的大,树叶儿象小鸟一样在骆驼岭上飞舞,被寒风摇曳的树枝儿发出“嗖嗖”的怪叫。我走在小四的前面,欢快得象一只小鹿,眼前是岭上青绿的桔树叶在寒风中抖动。过了这个冬天,知青点上的三十多名青年男女,用他们汗水浇灌的这片桔园,就要挂果了。极目远处,是农家村落升起的袅袅炊烟,小四突然问:“毛越你冷吗?”我说不冷,可我把头使劲往下缩的动作,表明我在说谎。她说,你转过来,我很听话的转过来,她把她脖子上的一条红颜色的围巾一下就围在了我的脖子上,我感觉不再受寒风侵袭的脖子顿时舒展了许多,温暖了许多。而小四却光着脖子,象树枝那样被寒风刮着,她额前的头发向后飘散,长长的睫毛眨动了一下,露出亲切的笑靥。这一年她二十岁,而我那时小她两岁。我很不好意思地把那条红围巾解下来,坚持要给她围上,我们就这样推来推去,最后围巾终于又围在了她的脖子上。
我们俩是去骆驼岭三公里以外的一个工厂小卖部,为知青点购买咸菜。我们俩一人手里拿了一个网兜,下坡时我们选择了一条近路,但坡比较陡,小四说毛越来,把你的网兜给我,不然你在前面会滑倒,我说不怕,有几棵小树绊一绊就下去了,你可要慢一点,她很小心地就下来了。我们从骆驼岭上走下来,沿着可过一辆汽车且被两边冬灌的麦田相夹的泥土路,朝工厂小卖部走去。可是,当我们买了咸菜回来,就没有那么顺利了,灌满麦田的水淹没了一段路面,路东边麦田里的水漫过路堤流进西边的麦田里。看到这,我和小四都犯难了。我弯腰挽裤腿,她问我你干啥呀?我说咱们走过去,说完这句话时,我已经把袜子和鞋提到手里了,她却很难为情地站着,我问她你咋啦,怎么不脱鞋?她不好意思地说我不能下水。我说你怕水冰是吧,来,我背你过去,她说你先把两网兜菜提到那边去放下,你再过来接我,我把两个网兜提上,从冰冷的水中过去时两只脚都快麻木了。她执意不让我背她,她说你背不动,要不这样吧,你在路边捡几个石头放在流水的那段路上。于是,我捡了三块石头放在流水的那段路上。她就走过去了。我们按原路,又走到那个陡坡的地方,她说她先上,我上去了就来拉你,于是她提着兜先一步一步地攀上去,把网兜挂在上面的一个树杈上然后又一步步走下来,先是接过我手里的网兜,然后又伸手来拉我。
当我们回到骆驼岭上的时候,风已经停了,铅灰色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雪,瞬间就覆盖了我们走过的那条细长的小路,小路上干枯的茅草一下落满了毛耸耸的雪,打眼望去,就象摆放在桔园边的白飘带。雪花儿静静地在骆驼岭上飘落着。不多的一会儿,桔树的叶片上就缀满了一团团雪,很象盛开的白莲花。我们都朝着岭下的那条路上望着,在茫茫雪雾中,依稀可见那座工厂,在那条类似街道一样的路上,出现了一股人流,工人们已经下班了。远处的村落也已经看不见炊烟。只能看到雪花的静静飘落,于是我说了句“瑞雪兆丰年”,而小四却说:赶快招工!
时过境迁,如今我们骆驼岭上的那批林场知青,现在都按部就班的在各个企事业岗位上发挥着作用,我们对那段艰苦岁月中的友情,多少有些依恋。二十年过去了,然而小四却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度过二十年知青插队的庆典,就过早的离开了人世。这使我想到,一个人的生命是多么短暂,有时还来不及回首往事,生命就提前走到了你人生旅途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