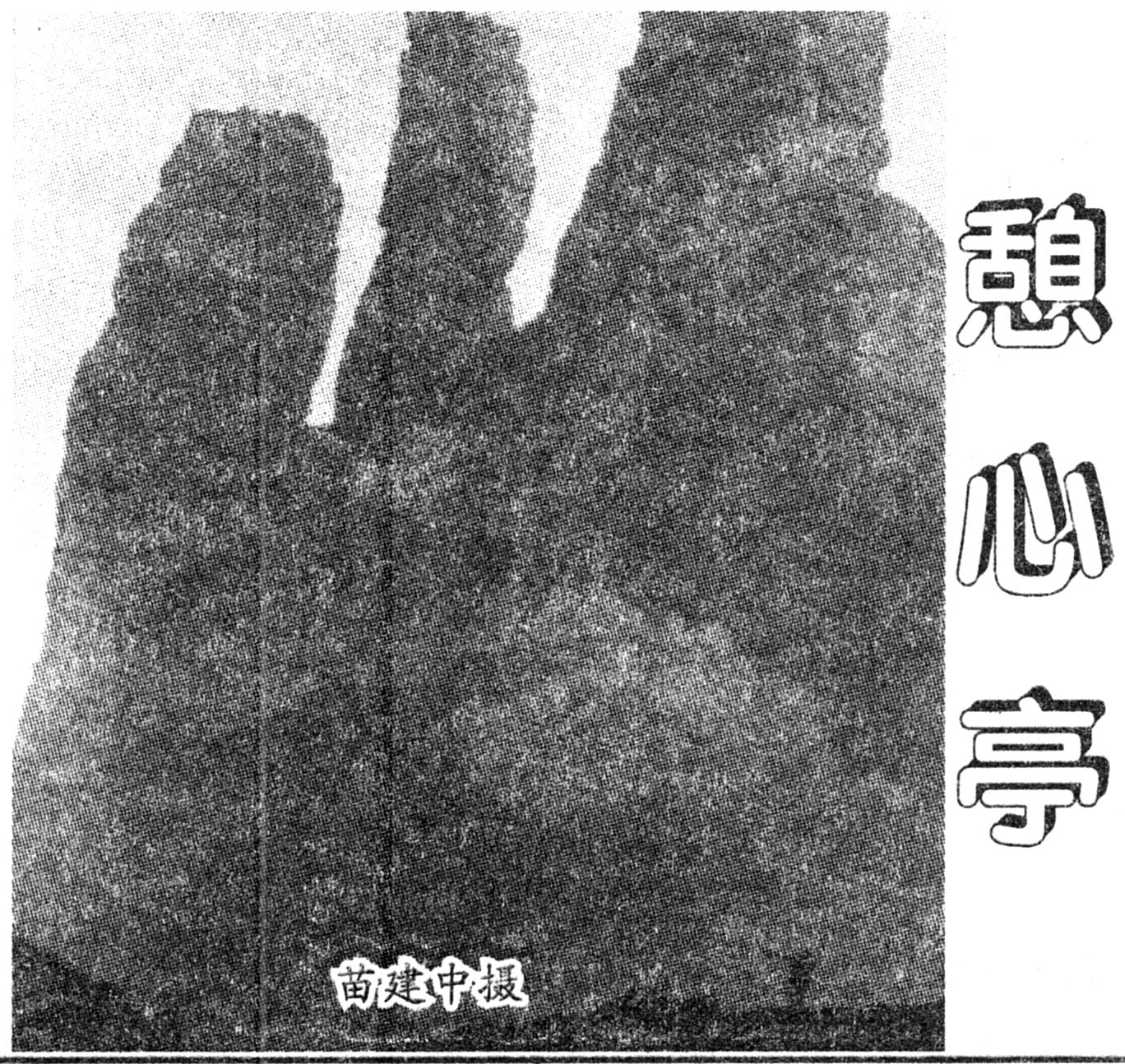文/齐国华
我小时候见到的西瓜,个儿大、皮皮薄、熟得早、色泽亮、瓤儿沙、味儿甜、籽儿少,十分赢人,但却很少吃到。那一年,家里盖了两间草棚,饥荒拉了一屁股,日子过得很不景气。刚放暑假,父亲就让我去镇上给猪拾瓜皮,来回要跑三十多里路,又没有水喝。母亲怕我渴,向邻居我婶借了五分钱,嘱咐我去镇上渴了顺楚买牙瓜吃:我高兴地提上背篓直奔小镇。这天,天气热得厉害,镇上人不多:我提着背篓守在一家瓜摊旁,头顶烈日,脚踩烫土,不时地打量着客主,等待着一块块瓜皮。望着人家手里那红艳艳的瓜瓤,馋得我直流口水;渴得实在忍不住了,在买主离开后,便抓住时机狠狠地啃上几口拾到背篓里的瓜皮,美美地过过西瓜瘾。有时,遇到吃瓜的人少了,我便双管齐下,既拾瓜皮,又捡人家吐出来的瓜籽。说来那个年头,不论是生产队还是私人家庭都不富裕,但人们很厚道,十分注意节俭,吃瓜时从不浪费,直到吃净瓜瓤为止。所以我拾的瓜皮历来都是青一色的,我想啃带瓤的瓜皮还要买主恩赐。记得新闻媒介有过报道:说是西瓜皮营养丰富,可以做菜吃。由于家里经济拮据,西瓜皮在我家早就变废为宝:薄的喂猪,厚的切成丝,炒了当菜吃。整整一个暑期,我拾了二千多斤瓜皮,在山间羊肠小道上行程近六百多公里。
圈里的小猪就渐渐上起了肥膘。家里人瞧着我油黑发亮皮肤,夸奖我是一条好汉了。
正逢“全国山河一片红”时,我上了初中,学校离家六十华里,必须住校。我心里却很不踏实,常常为交生活费而犯愁。有时为买几毛钱甚至几分钱的学习用品也要伤心几次,家里平时没有收人来源,生产队里每个劳动日才四分钱,而且年底才能分红,全家只能寄希望于养头猪卖点钱来补贴家里的油盐酱醋等。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钱,整天是饥一顿,饱一顿,瘦得三根筋撑着头。当时,学校里整天是学工、学农、学军,上文化课的时间极少,加之课本不齐,缺这少那,听讲时,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天天盼着放暑假。这年暑期,生产队里种的五亩特种西瓜未等成熟,就吸引了方圆三十里开外的客商前来谈生意,因为这年种的西瓜,二十年来没有见过的,那瓜皮表面的花条纹像菜花蛇——绿中拌黄,深浅不一。更为奇特的是那洁白的瓤儿,血红的籽儿,像点点红梅闹雪,吃起来甜的渗牙。另外,作这特种西瓜的三个“小诸葛”认真实践了当地流传的顺口溜:“苜蓿地里种西瓜,窝施油渣畜粪加,花开水足蔓平铺,作务精细打野杈,西瓜熟了不用跑,招来嘴馋神仙家”。队里的五亩西瓜丰收,众乡亲喜笑颜开。一日,生严队长拿着话筒吆喝男女社员给某单位运西瓜,我也加入了运西瓜的行列,谁知事不凑巧,一不小心碰破了一个西瓜。队长发现后,大发脾气,随之宣布要我赔偿五毛钱。我羞涩地抱着西瓜回到家。家里人问明原委后,都默不作声。我知道是为这五毛钱发愁。善良的母亲终于开口了,她说:“这瓜就当咱家买的,咱们一起来尝尝新鲜。”俗话说:“泥瓦匠住草房,卖盐的喝淡汤。”虽然队里种着西瓜,可就是吃不起。望着这白瓤红籽儿的大西瓜,我有意寻了个借口想避开,好让整日为我们弟妹操劳的父母多吃几块,但慈母严父还是为我留下了两块,相互推让之后,我端到手里却又让给了弟妹。我只把收集在一起的瓜皮又重新“加工”了一遍。如今,已是九十年代了。兜里有了钱,吃西瓜已没啥稀罕。多年改革,城乡巨变。我们山里人告别昔日那种日图三餐,夜图一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循规蹈矩的生活模式。深山沟里真真正正火起来了。川里人说我们的深沟沟、山坳坳、岔岔路、旋涡地变化了;说我们的荒山野岭水秀山青,景色迷人,今非昔比。去年七月七庙会,寺院门前人山人海,卖吃食的摆了两行行,光西瓜摊就占去了一大半。吃瓜的男男女女瞧瞧这边,瞅瞅那边,择选称心如意的瓜摊。一对城市来逛会的青年恋人,买了一个约有十斤重的瓜,吃得很跷蹊,每牙吃两口便弃之一旁。看到这种现象,我十分反感。
前几天,去某机关办事,正巧碰上了“西瓜宴”,熟人顺手递来一牙瓜,我便吃了起来,看地上如山的瓜皮,我的瓜皮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且与众不同,除和别人的一样少了红色外,还少了一层瓜皮肉。在一双双眼睛的扫视下,我红着脸放下了手中的瓜皮。此时,我无法猜度他们是赞扬,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