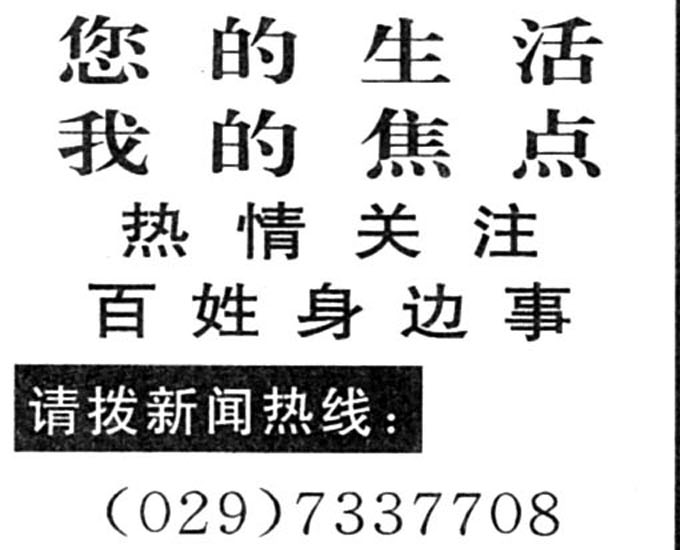1971年秋,我们家买回了一台上海牌缝纫机,成为家中唯一的奢侈品。
母亲怕把它磕坏了划伤了,恁是给机头套了个厚垫子,又给机身做了件厚罩子。十三岁的我哪在乎母亲给议订的“纪律”,偷偷地踩空机子,悄悄地穿线缝布条,哪料缝纫机罢了工,在挨了无数拳头之后,我竟然做了个花书包!
在企盼中,我迎来了十七岁,在缝纫机密密匝匝的针迹中我踏上了下乡之路。每次回家,我总背着一包旧衣缝补。在朦胧的目光中,用颜色相似的布料补肩头,用两块半弧形的布块补屁股窟窿,对称地补膝盖疤,熟练地加长裤边……缝纫机不仅教会了我自己动手艰苦朴素,而且是我迈向人生克服困难的第一师!
1983年结婚时,母亲将这台缝纫机做了我的嫁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缝纫机已不再是破衣旧补的拼凑者,不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机器,而是缝制各式服装装扮亮丽生活的有功之臣!
然而没过十年,忙碌了近三十年的缝纫机不得不“退役”了。“做衣不如买衣”的观念彻底冲击了我对它的一片痴情,于是忍痛将这位半生的朋友请上了阳台……缝纫机,便成为春天沧海桑田中一个故事。
(武长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