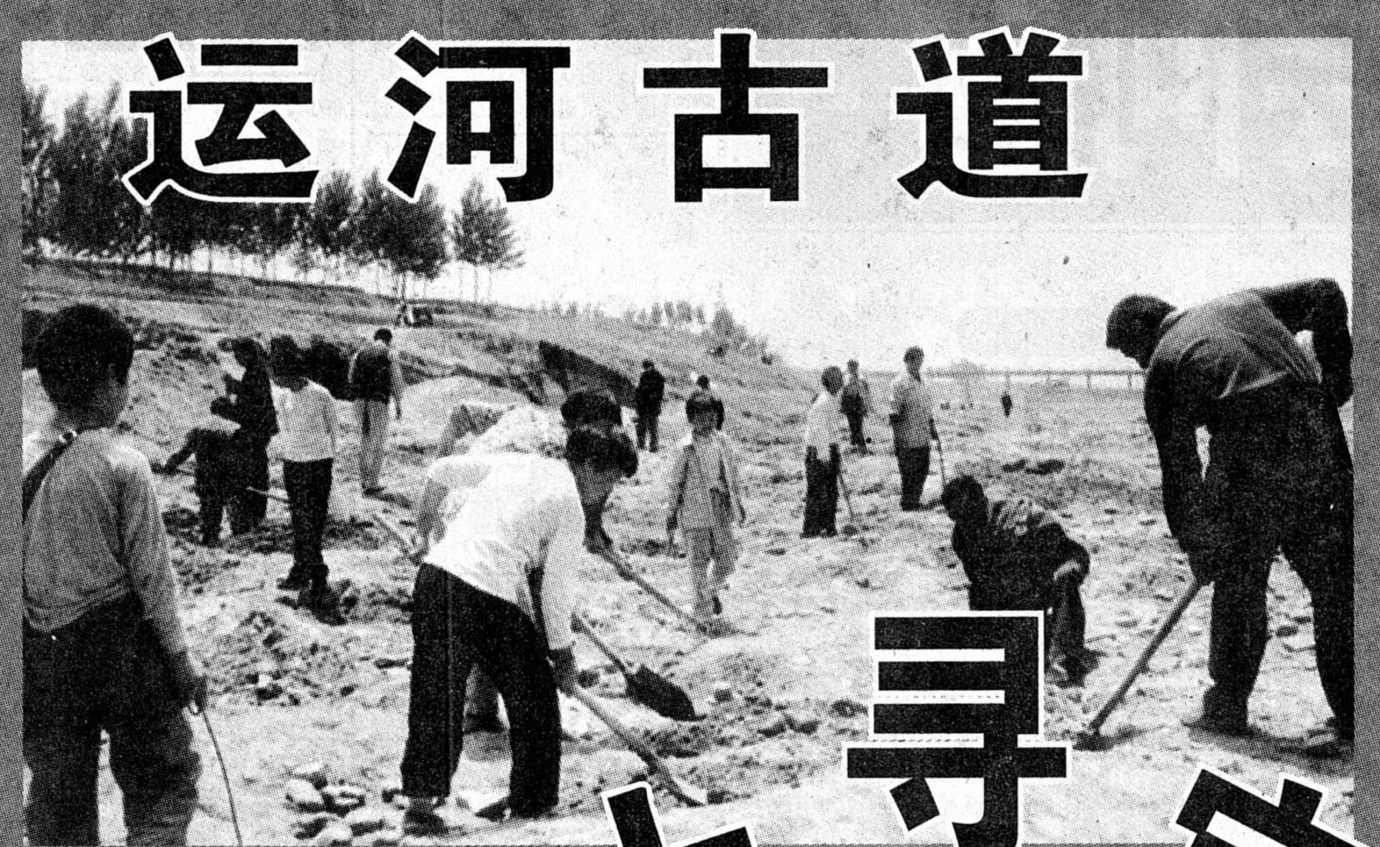文/丽娜
1903年春天,在巴库,一个两岁的女孩在海边玩耍时不慎被海浪冲走了。24岁的英俊青年斯大林看到这一情景,跳进海里把她救了上来,用宽阔结实的胸膛温暖着那个小小的身体。
1917年夏季的白色恐怖日子里,列宁就隐蔽在娜佳的家里,这时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的斯大林已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职业革命家。作为娜佳父亲的老朋友和列宁的战友的斯大林,如何也无法将14年前他所救的婴儿和眼前的她联系在一起,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有着微黑的肤色、鸭蛋脸、柔和的棕色大眼睛,带着某种东方多愁善感仪态的16岁女中学生。
这时的斯大林已经有了妻子。她是卡捷林娜·斯瓦泥泽。她也是斯大林的同乡格鲁吉亚人,而且是梯比利斯一带有名的美女。可惜的是,这段美满的姻缘持续的时间不长,在他们的儿子雅可夫刚刚两岁的时候,她就去世了。
当斯大林失去了第一个妻子,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娜佳不顾年龄上的差异,毅然来到他身边。和斯大林结合后,她马上就随丈夫去了莫斯科,在弗琪耶娃领导下的列宁秘书处工作。不久以后,又随斯大林一起去了最为危急的南方战线。娜佳当时18岁,而斯大林是40岁。
为了缩短她和斯大林之间的差距,她很少和孩子们在一起,但留在她子女印象中的妈妈却是一位受尊重、聪明、美丽、对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的好母亲。只有她能把这个家庭中性格各异的亲属全部团结起来,使之和睦相处。在家庭团聚的时候,她甚至还经常为大家轻盈而优美地跳一段格鲁吉亚快步舞。
娜佳深深眷恋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她有着平静而舒适的生活,她受到人们的尊重。但她内心中的独立和自尊则更令人称道。
在工学院上学期间,她不让汽车去接她,从来也不说明自己是谁,同学们根本就没有把娜佳和斯大林联系在一起,她是个极聪慧的女人,心地又极其真诚,一旦被一个人征服,就永远把自己交给他。但她与斯大林年龄和经历上的巨大差异,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的。斯大林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他主宰着一个最大国家的命运,这就决定了斯大林要具有钢铁一般的果断、沉稳甚至是冷漠和专横的性格。而娜佳对他这个内心世界的了解毕竟还是幼稚的,她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这个伟人。这种衡量和希望她又从不愿说出口,因为她是个自尊心很强的、性格内向的人,当她情绪不好的时候,她从来也不承认心里有什么事。
对她来说,斯大林逐渐变成了一个极其生硬、极不善于体贴人的人,他已不是她青年时期所憧憬的那样的人了。而她又仍然爱着他,这使她十分苦恼、也十分失望,她把自己比喻为一个殉难者。他们之间开始爆发了谁都认为对方是不可理喻的争吵。1926年的一次争吵后,娜佳一气之下带着儿子瓦西里和女儿斯维特兰娜回到列宁格勒的娘家去住。不久后,斯大林从莫斯科打电话去“求和”,并表示要接他们回家去住,娜佳却在电话里不无挖苦地说道:“你来干什么?这对国家来说代价太高了。”但她又每每为斯大林给她的温情而欣喜。一次会议后她深夜归来,十分疲倦,斯大林抚慰着她,体贴地扶她睡下,她说:“看来你还是有点爱我。”……她是多么希望这种她认为是十分吝啬的爱能持续下去,然而最终仍然是失望。她曾不止一次地向好友和亲戚表示想要离开斯大林,但又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
在苏联高层领导的夫人们的圈子里,娜佳逐渐变成一个不被人理解的人,她们说她太严格,太严肃,和自己的年龄不相称。这就更加深了她的苦闷和孤独,这种自我抑制,严格的内在的自我纪律、精神上的不满、委屈和愤怒,使压力越来越大,最后终于爆发了。而导线的本身却又是那样的微不足道。1932年11月7日晚上,克里姆林宫为庆祝十月革命十五周年举行盛大的节日宴会。党政的高级官员、外国代表的贵宾云集,气氛极为热烈。情绪很好的斯大林当着大家的面喊娜佳:“喂,你,也来喝一杯!”在这种正式场合,他应遵循礼节叫妻子的名字和父名,或叫表示亲密的爱称,斯大林忽视了。从来就认为自己不是属物的娜佳感到受了羞辱,于是大喊一声:“我不是你的什么‘喂’!”接着站起来。在所有宾客的惊愕中退出了全场。
第二天清晨,克里姆林宫官邸和平时一样是宁静的。管家瓦西里耶边娜准备好了早餐去叫斯大林夫人。推开门,她惊呆了:娜佳躺在血泊中,手中握着一支“松牌”袖珍手枪,尸体已经冷了。
娜佳的死给了斯大林极大的震惊: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她要自杀来惩罚我?难道我不善于体贴?难道没有把她当妻子去爱?难道没有尊重她?难道少陪她上几次剧院就那么重要?
最初几天,斯大林的精神几乎崩溃。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他手扶棺木悲哀地沉默着,却再也没有力量去参加葬礼了。他对娜佳的嫂子说:“我也不想活下去了……”娜佳的嫂子和姐姐日夜守着他,担心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
娜佳生前用一个家庭主妇的手亲自转动了这架和睦的家庭机器。她的哥嫂、姐姐、父母亲都与这个家庭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连受到斯大林冷淡的前妻的儿子雅可夫也在这里感到了温暖。而她离去以后,维系家庭的纽带也不存在了。亲戚们很少来往,即便来往也经常发生争吵。娜佳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舅舅、姨夫、姨妈,大多在“大清洗”中受到牵连,甚至含冤死去。
娜佳的死成了斯大林心底深处一块永远流着血的伤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那些他主观上认为造成娜佳死的因素越来越痛恨,经常咒骂娜佳生前读过的书籍,咒骂娜佳的好友波琳娜·谢苗诺夫等,咒骂送给了娜佳小手枪的巴维尔(娜佳的哥哥)。但对娜佳的怀念也越来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