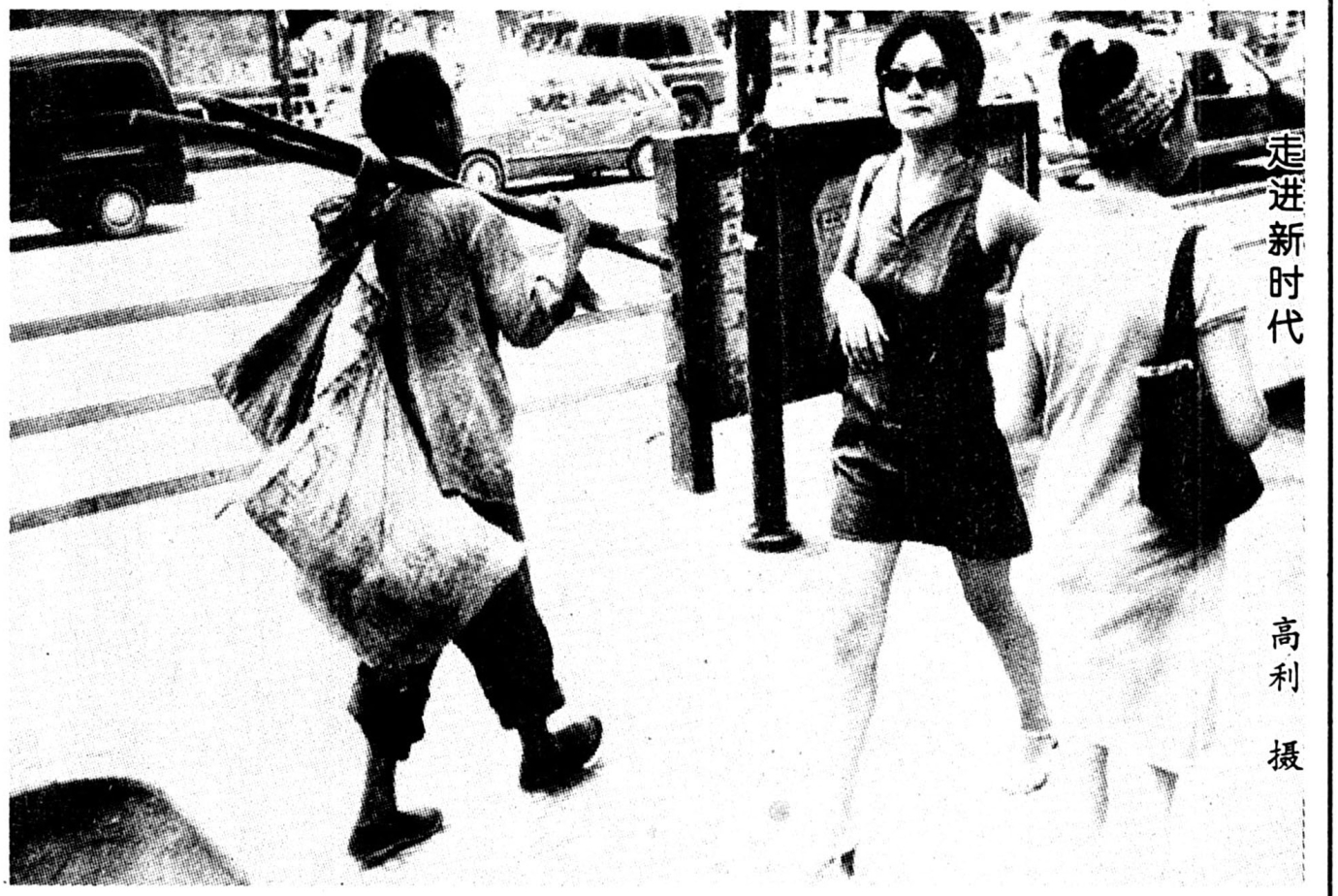文/韩小士
像大熊猫、白鳍豚一样,善良在我们的生活中已成为一种越来越稀有的东西。因此想触摸善良,就如想触摸那些日益稀少的动物一样,成为总在心头萦绕的念想。
有个周末在机关值班。周日清晨看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脸上老挂着闻名遐迩的“坏笑”的崔永元这一次一脸严肃,他给我们介绍的嘉宾是一位名叫史国良的青年画家。史先生开讲不久就涌出泪水,哽咽不已。他在回忆34年前的事情,由于彼时的无知与幼稚而去“革命委员会”告发班主任,使得在课堂上偶然有一句口误的老师受到“无产阶级专政”,被关进粪尿四溢、蛆虫乱爬的厕所里。当9岁的史国良良心发现,偷偷地给老师送西红柿时,这位善良的女教师没有埋怨一句,甚至还说,这是我今年第一次吃西红柿,真好吃。这时,她的双脚已在粪尿里泡得发胀变形了!这是何等善良的一位中国妇女!当她出现在演播室时,观众席上爆发出经久的掌声,人们在向这位名叫申世恩的老师致敬,此时的她,已经是步履不太灵便的老人了。
机敏睿智的主持人崔永元在此刻频频拭去眼角的泪水,而我亦禁不住潸然泪下,面对着这么一个善良的、宽容的中国女性。申世恩老师在节目中说:“史国良当时是一个孩子,他也是被利用的呀!”这又是一位有着多么深刻思想的智者的语言!
如果说在这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就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了善良的话,值完班以后去看影片《洗澡》,则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善良。当然,这种感受充满诗意,与《实话实说》这样的谈话节目不同。在影院中得到的,除了人性中向善力量对自己的感染以外,这个过程还是一次艺术上的审美行为。
《洗澡》作为反映当代百姓生活的故事片,应该说没有什么太抢眼的“卖点”。它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漂亮的女主角(从严格意义上讲,甚至没有女性角色);更不是什么“大制做”,主要人物也就是父子三人,他们这部片子吸引我的,主要是充溢在影片之中汩汩流水一般的善良。
父亲老刘师傅终生厮守着“清水池”这间不起眼的老式浴池。大儿子大明则南下深圳发展,在影片中出现时颇有点衣锦还乡的味道。最出戏的,倒是小儿子二明,一个从来没离开澡堂子的傻子。
二明在影片中的作用,依我看来无疑有一种隐喻色彩,这个人物应该是编导心中“善良”二字的代名词。《洗澡》中二明的形象是不是对那些逝去或即将逝去的美好情愫的一种呼唤?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笑又显得是多么无力,因为二明是作为一个“傻子”出现的。
常来“清水池”的顾客中有个爱唱《我的太阳》的胖小子,这是个有心理障碍的角色,必须站在淋浴喷头下才能引吭高歌。其他人中就有不满者,嫌吵,动辄就把阀门关了,那响遏行云的歌声随之戛然而止。此刻出来抱打不平的恰恰是傻子二明。想到这一出戏,我就思索,对那些普普通通的百姓来讲,“善良”不啻是滋润精神家园的甘露,得了“善良”的滋润,在小澡堂里洗澡的芸芸众生才能放开喉咙高歌一曲。因此,影片末尾,老居民区拆迁,在居委会组织的小晚会上,二明手执水管给台上欲唱无声的胖小伙兜头浇下这一看似荒唐的情节,就有了一个坚实的情感铺垫。不但能使观众接受,而且能在大家心底引起一阵共鸣。二明无疑成了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中最善良的人,
触摸善良有时是很容易的。比如,周日早上收看了《实话实说》,认识了远在北京的申世恩老师。比如,同一天的上午连看了两遍电影《洗澡》。
我居住的这座城市的电影公司有个特平民化的规定;周六周日的第一场电影为“合家欢场”,票价一律五元,所以,那天切切实实地触摸傻子二明的至纯至真的善良时,我的付出实际是很少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