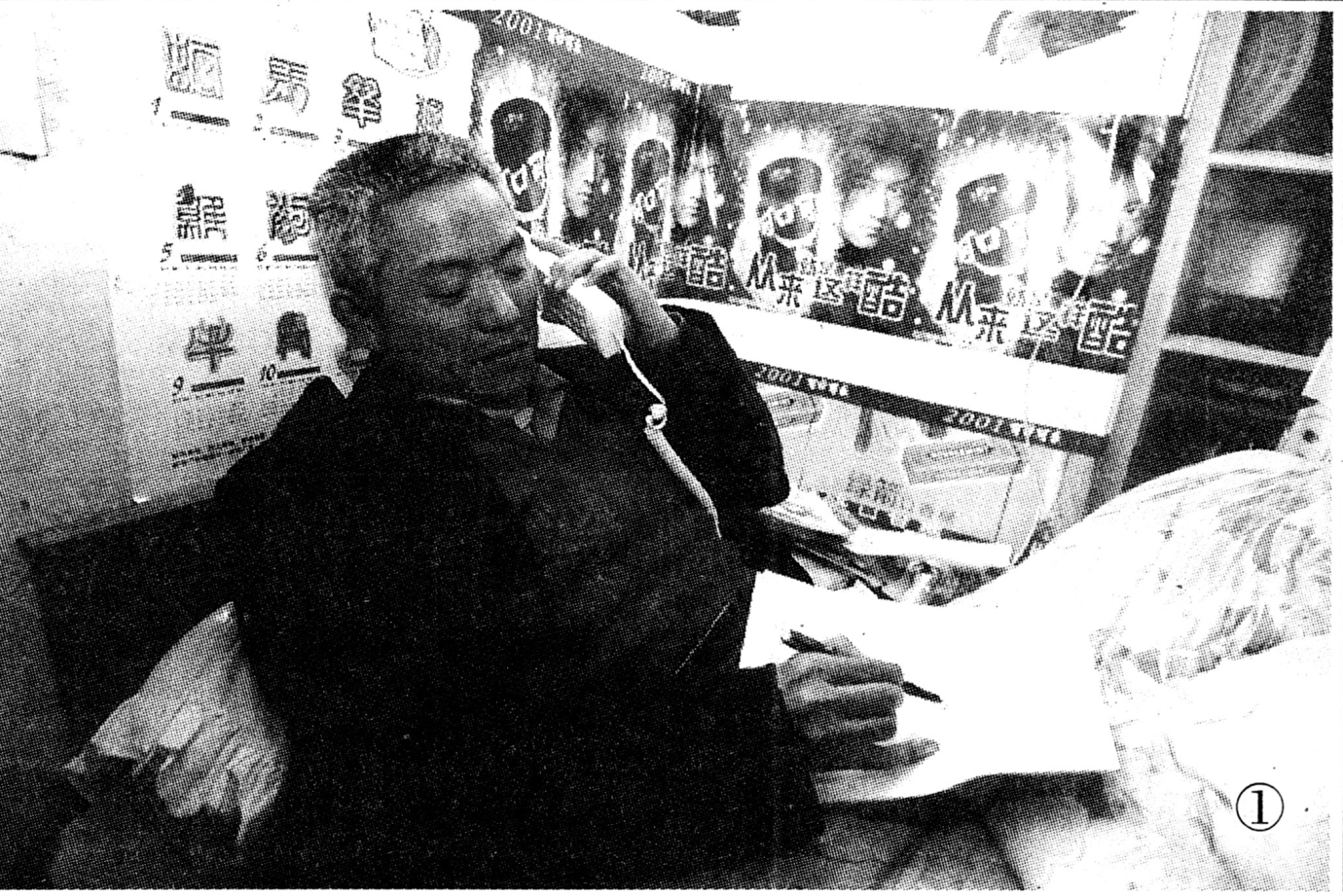“人的归宿越简单越好,我死了以后遗体捐献给医院,任由医院怎么处置……”75岁的延光厂退休工程师汤亦新表述他的这番心愿时,全然忘了正在打吊针,他的右手不由自主的上扬下放,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担心针头滑落。其实,汤亦新的遗体捐赠申请已获得了批准,当他拿到第四军医大学病理学教研室登记接受站签发的编号为6、7号的西安市公民生前志愿捐献自身遗体登记表时,表情相当平静,他的妻子徐学仁也同样取得了申请表。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庭。早在90年代初汤亦新老人就萌发了死后捐赠遗体的想法,可当他向单位领导提出这个“要求”时,大家犯了难,上哪去找这样的地方,此事不了了之。
后来汤亦新听说第四军医大学接受捐赠,不顾高龄,开始了奔波,此时他的妻子已患了癌症,要求把她也算上,去世后遗体供病理研究。
说起无偿捐献遗体,汤老说,人生的经历让他淡视名利,何况身后事。解放前,他在国民党的航空公司任机械师,1949年两航公司(中国、中央航空公司)员工宣布起义,他和同事们分批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先后在太原、西安等地工作,中间尽管有些不如意,甚至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可他总认为没什么过不去的坎。1985年他从延光厂退休,闲暇之余,总在回顾人生,他看不惯奢侈靡华,总想着身后事越简单越好。当时汤老给退休办领导写过申请,提出了四条,他过世后一不出讣告;二不接受礼品;三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四不留骨灰。他还特别提出过世后,谁一定要送礼,就送给希望小学。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汤老仍不忘祖国的医学事业,他动情地告诉在场者,中国的医学院,平均4个大学生解剖一具尸体,原因就是尸体来源太少。许多国民宁愿火葬甚至土葬也不愿捐献遗体。在国外,一个医学院大学生平均要解剖4例尸体,外国人的思想观念要比国人开放得多。在国内,沿海大中型城市市民又比内陆人士开明。谈起一些人为自己或亲人修建豪坟,汤老气愤地说出了两个字“无聊”。 本报记者 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