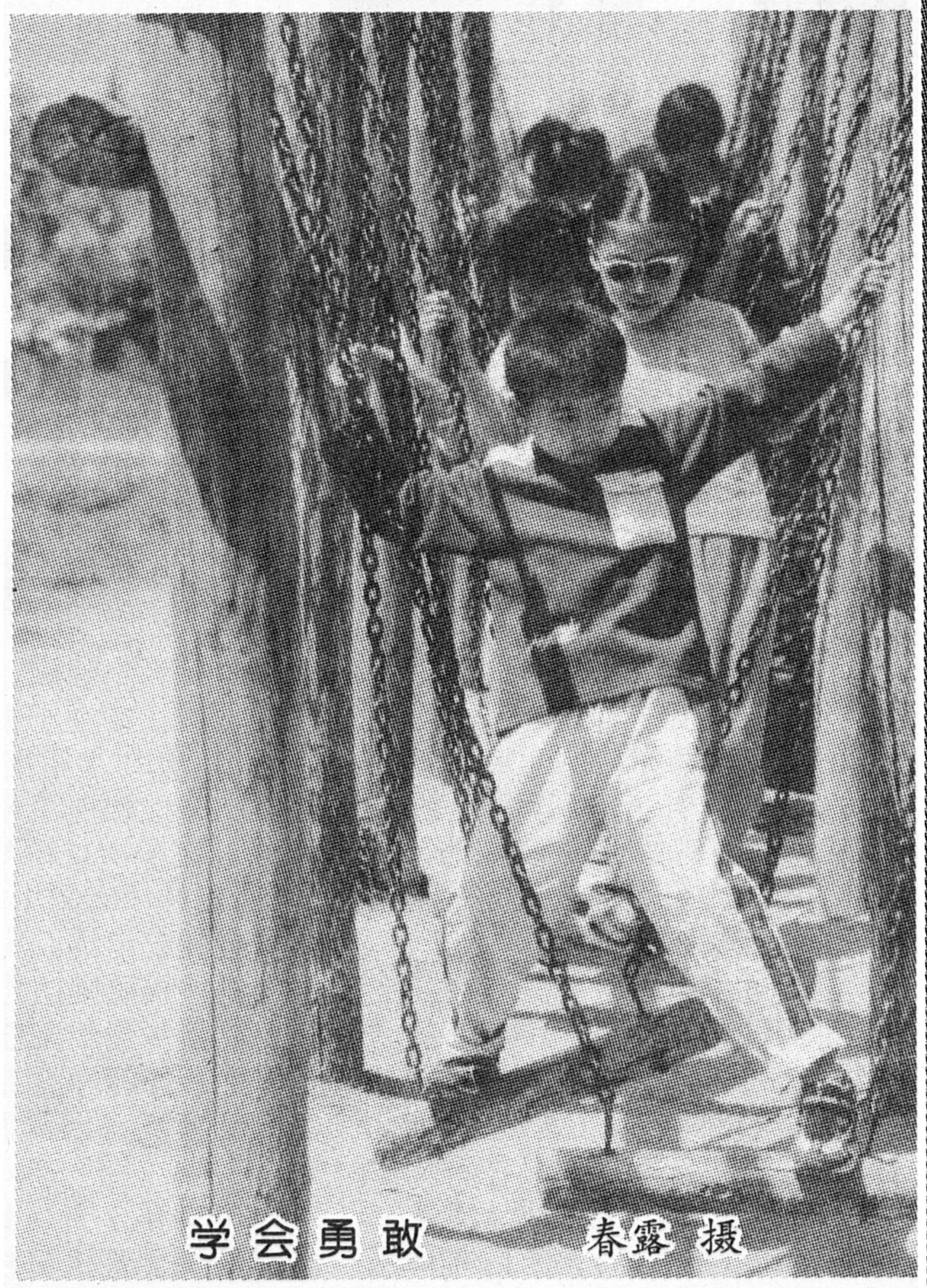小说 □文/简飚
那是一个起风的傍晚。我站在一级公路的一个没有站牌的路边,等—辆去机场的出租车。
等了很久,偶尔有“的士”飞驰而来,也是从身边旋起一阵风后又疾驶而去。我看了看表,这已是一个耽搁不起的时间了。我向车道方向移了移,准备感动上帝。其实那些司机们一定看到我这个站在风中穿米黄色茄克衫的小伙子,正拼命喊着挥摇着手中的接站牌。
“吱——”,一辆车从天而降,竟然在我的面前!一个中年男子从车里探出头来问我:“请问师傅,去机场怎么走?”谢天谢地,这简直太富有戏剧性了!我尽力节制住心底的喜悦。“哦,去机场?还远着哪!这样吧,我正要去接人,顺便搭车带个路吧。”我几乎未经他的允许就上了车,车内已经坐满了人。除了司机和司机右侧座位上的小女孩,一对夫妇模样的中年男女坐前排,一对夫妻模样的老年男女坐后排。我是多余的人,只能站在临近车门小女孩座位后的那块平板上。司机似乎不高兴,从我对角面向的窥镜中,我看到一双近乎冷酷的眼里多了几分寒冷。
车启动了。但我感觉到由于我的出现,车内的气氛立时显出几分紧张,车里人的眼睛都不去感觉我的存在,我像是他们路边拾着的一个行李,或是半路上抓来的一名囚徒。可能是我一米七的高度搅乱了人们的视野,那位男子很客气地要求我坐在凸出的那一条挡板上。我服从了。我注意到,他们的眼睛虽都平视在车座前的玻璃上,但目光里仍不乏对我的厌烦、轻贱甚至敌视的神色。
我把头偏向车外,木然地看着道路把风景一帧帧闪过。去机场还有20公里,但我在车内呆一分钟便有一分钟的不自在。我想赎回那被剥夺了信任的权利。我把话抛给中年男子:“出差呀?赶哪趟飞机?”中年男子刚哼出两声,那位中年妇女便把哼声掐断。我讨了个没趣。前座的小孩正在翻一本连环画,这时候突然扭转头来告诉我:“我和我爸爸妈妈送爷爷奶奶去北京。”我赶紧“哦哦”地点头。想必,小女孩是唯一把我当好人的人。
一个趔趄,车停住。司机问我去机场的路,我才知道到了分岔路口。这也是我最担心的。虽说去过几回,但我历来是不记路的人。我说,我问问吧,这里好像变了个样,想不起来了。车外三三两两的人涌过来,车里的人眼睛顿时对我多了几分仇恨与警觉:谁也不能断定这些人中没有我事先约好打劫的同伙。后来还是司机精明,把我关在车里,自己下车问清了路才踩响油门。
我真像是个犯了罪的囚犯。等车刚开进机场,我立刻跳下车,竟然没有说声谢谢,也没有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