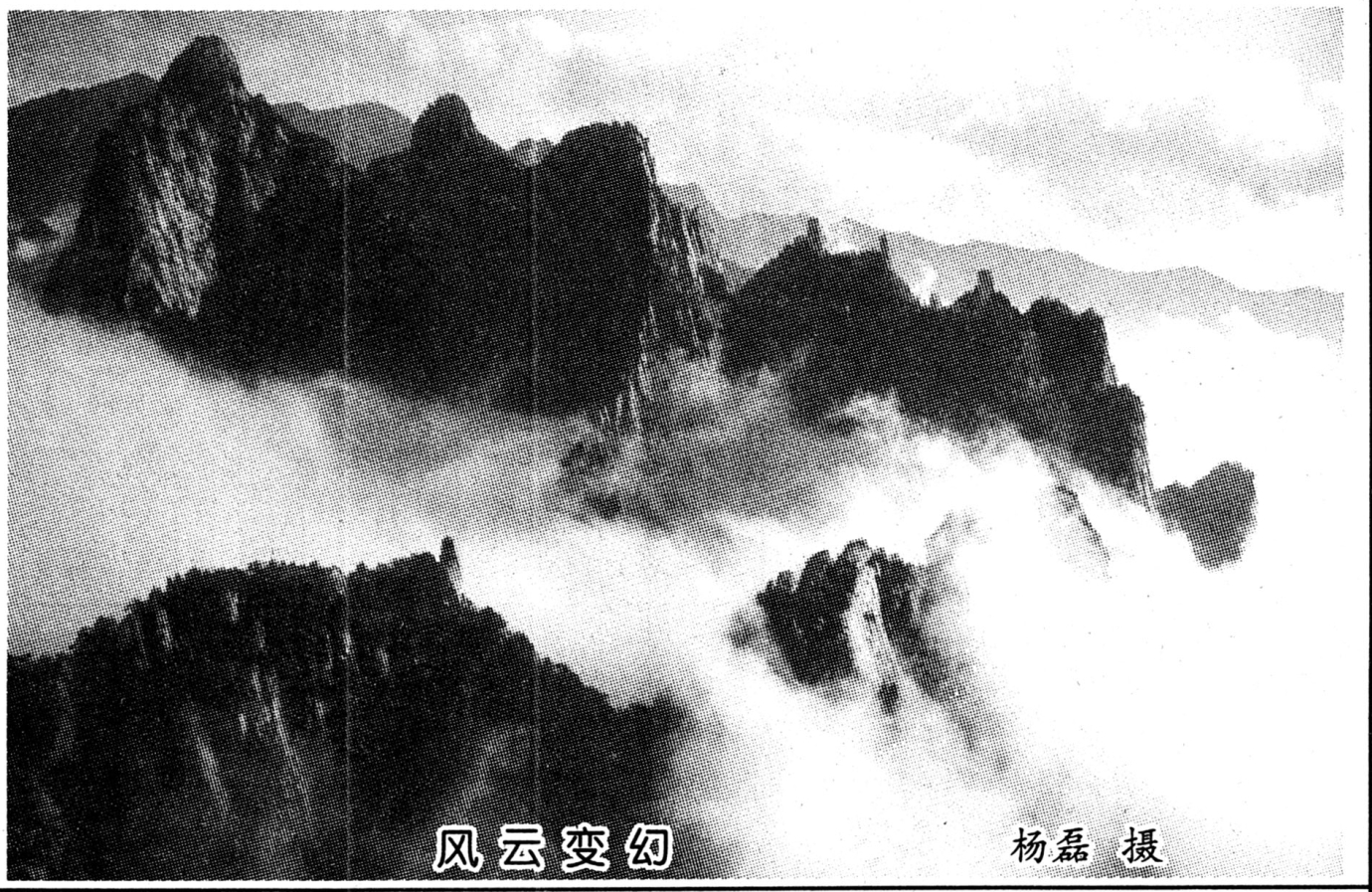散文 □文/陈绍龙
春了,我漫山遍野的呼唤你的名字。
是野菜。
踩一踩松软的土地,冬在一地散落的稻草上着满毛茸茸晶亮的花边,似乎只是不大的功夫,风便把它吹成了弥漫的柳絮。有两支触须开始从地罅里探出头来,两只手,紫红紫红的,象是从母体里分娩出来沾着的血痕,一寸、一寸,仄身振臂,于是十支、一百支、一千支、一万支的小手呼拉拉地伸出来了,在田埂上叽叽喳喳的闹——是双芽子!
叮叮叮…操场上篮球是最活跃的,学生看,村上的人也围着看。大孩子在操场上打,我们只得站在篮板后面,要是有谁投球失手,不着篮边,我们就会捡起来,急急地跑到篮下用力朝篮里投,大孩子叫我们“端马桶”。我自然是不着边儿,引得一操场人的笑,尽管如此,我还是会站在篮后,再等,太阳偏西了,我才想起操场边有一只空荡荡张望我的竹篮。我只好回家撒谎,说老师布置的作业多,没空。家里人当然不信。妈妈呵着嗷嗷叫着的猪,我就一声不吭的去写大字或找禾纸擦灯罩了。
不上学的日子总是很多。家里面为我们备的最多的就是小竹篮和挑菜的手锹。一个人,或是一群人,蹲在田野里挑菜。是青的就有名字,见着的差不多我都认识。蒿子最多,有黄蒿、白蒿、狼尾巴蒿,这都不是名贵的野菜。起先我们是不挑它的,有时我们贪玩,自己的竹篮实在是挑不满了,才匆匆的挑着充数,当然也只是把它放在篮子底下,好让家人觉着我挑的都是好菜。要是我们去的周围没有蒿子就惨了,我们就把半篮子菜放在水里泡,让它在水里膨胀。泡着唱着:“抖弄弄,鲜弄弄,去家胡弄老公公,哦——”
谷谷丁有浆,养猪;田七要嫩的,它有刺,不过要是谁挑菜时不小心把手划破了,我们就会把它嚼烂放在伤口止血。桃儿杏儿刚开花,童年总是有一张馋馋的嘴,有一只怎么也填不饱的胃。我们去找酸溜子,酸溜子团团的绿,细碎娇小的样,我们把它放在嘴里,只是为了咂吧出一丁点的酸味。
人能吃的野菜也不少。荠菜最好。荠菜小菜地多,不过,有谁家的菜地里的荠菜舍得让人挑呢。苦味苔要去芯,然后再用开水在锅里拉一下,留着包饼或是熬粥。我常到我门旁的刘婶家大着胆子尝。我呲牙裂嘴的,常惹刘婶的笑,刘婶就用大口很有滋味的样子吃给我看。因为太苦,吃苦味苔的确是要勇气的。有一次在大场上我瞧着刘婶站在场上挨斗,原本浮肿的眼睛又泛红了,我才知,队上种一种红花草的留作绿肥的植物,刘婶曾去偷回家吃……
春了,一阵阵泥土的气息向我袭来,伴着青草和野菜味儿,我分明听到一群群儿时伙伴的嬉笑声来。
周末,我们一家三口到淮河滩放风筝。一簇簇笑语,逐日,逐风,仰之弥高,我和爱人却在意起河边的野菜来。我找到一棵,爱人说先别急,要我说出它的名字,我就要她先说。她找到一棵,又叫我先说它的名字,我们就齐齐的叫着——一字不错!我们满湖满野地呼唤儿时的伙伴的名字,我们兴奋得手拉手跳了起来,象一对挎篮执小菜锹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