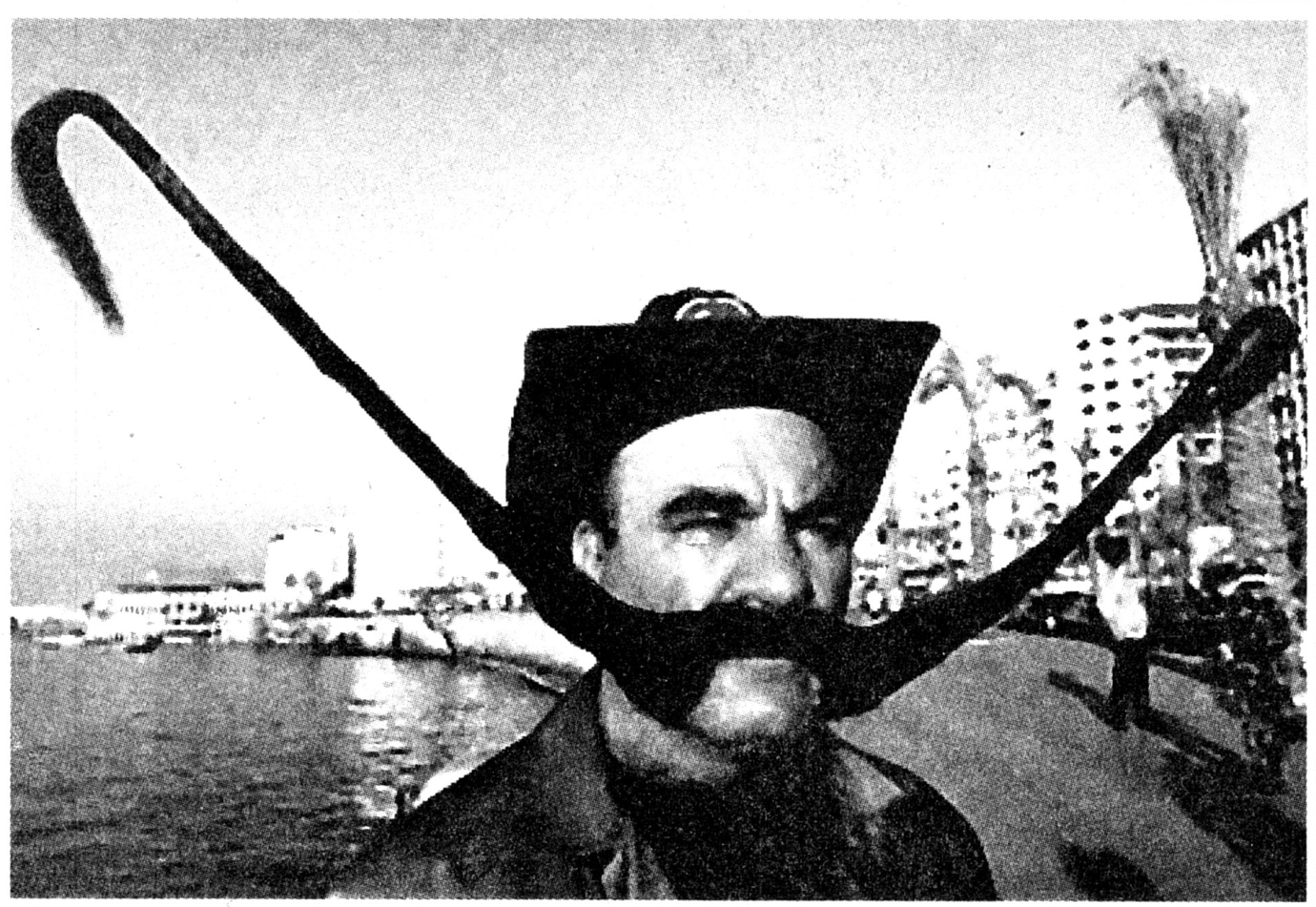□文/李而亮
进入6月中旬的北京,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清爽宜人。大地绿树葱茏、繁花似锦,辉映着蓝天白云,让人格外心旷神怡。大自然似乎在尽情弥补着由于非典肆虐使北京人失去的春天。随着连日来的“零报告”,人们纷纷甩掉闷捂了多日的口罩,以脱离牢笼般的感觉走出家门。于是,街道、商店、餐馆、公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
笔者对此也怀着同样急不可耐的心情,一是闷的时间的确太长了,二是因为一场非典,全社会都对过去的不良生活方式和陋习进行了深刻反思,而且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速度制定了严治陋习的“重典”。借着宜人的气候,谁能不产生一种体验“重生”后新生活的欲望?但最近几天,本人到了几个档次不算低的餐馆和商场,全然看不到有明显的变化。就说大家嚷得最响的“分餐制”吧,无外是多增加了一双公筷。开始大家还有所注意,酒过三巡后,公筷早晾一边了;再说逛商场超市,测体温的只有极个别,戴口罩的顾客又成了大家注目的“稀罕”;食品被翻来挑去全然无顾忌,营业员在一旁带着捂嘴不捂鼻的口罩见怪不怪;更说那“万恶之源”随地吐痰,确实少了,但却有目标地吐向裸露的垃圾桶边、树根、墙角等地。反正躲的只是罚款,细菌会怎么飞是管不着的事。总而言之,让人感觉到非典提防之声虽犹在耳,一旦“解放”出门,就似乎已把灾难的恐惧抛到脑后。
如果说经历了一场劫难之后,人们对病魔疫情产生了藐视的心态,则当有理由为国人心理走向成熟而高兴,但要是产生麻木式的健忘,就有点可怕了。国人对灾难是否易患“健忘症”,我对此不敢妄下论断。但近年来,屡屡有此类受众人所指的事情发生,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对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健忘,有人就觉得圆明园的断壁残垣不雅观,呼吁斥巨资复建世界第一的“园中之园”;因为对日寇蹂躏中华大地的健忘,有人在生意摊上摆卖起了仿造的日本军刀、军服、军舰,更有出格者竟披着日本军旗在万众注目下登台演唱;因为对“文革”十年浩劫灾难的健忘,就有人独出心裁地将餐馆饭店全部按照“文革”风格装修,并让服务员身着全套红卫兵服装招待客人。据说由于迎合了许多人的怀旧心理,这样的餐馆饭店生意相当不错。巴金等知名人士因担心国人对文革的健忘而痛心疾首,大声呐喊,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以示后人。但一直未得到有力响应。相反“怀旧”的东西越出越多,“革命样板戏”越唱越响。
非典病菌无形无像(尽管在显微镜下呈冠状),倒不用担心会被人制作成玩具饰物什么的,让大家在一笑间忘记了它的凶残。但是,盲目的轻蔑、乐观的自慰,更能助长人们的健忘。我们许多人之所以善于以这样的心态来淡化灾难,因为最能娴熟运用的辩证法就是“一分为二”:坏事能变成好事,祸兮福所倚。非典的灾难还没有宣告结束,病原还没有彻底查清,疫苗的问世还遥遥无期,就有不少人开始盘点起非典灾难所能变成的“好事”了,什么,非典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国民经济影响有限、催生了多少个新的商机、激活了多少个行业和企业,等等。甚至在某些场合,“感谢非典”这样的话都喊出来了。诚然,我们不能否认,任何灾难的降临,都会促使许多因素的生长和转变。但这是与灾难奋力抗争的结果,而不是灾难本身包含着好事的成分。如果我们在看到局面的好转,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之时,淡忘了灾害曾给我们带来的劫难,淡忘了为之付出的沉痛代价和巨大牺牲,淡忘了灾难给我们带来的血的教训,在分享胜利成果时以为自己幸运地掷到的是“硬币;另一面,那么,得“健忘症”就不可避免了。
在本人写这篇拙文的时候,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我国除北京和台湾外,所有发生非典疫情的城市已解除旅游警报。看来,万众一心抗击非典这场战斗不久将会落下帷幕。中国戏曲有个很大的特点,不论是正剧还是悲剧,最后都会以喜庆的大团圆结局而收场。这使得观众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习惯,再悲再惨烈的故事,观众愿意在观赏的过程中将自己融进其中,酣畅洒泪,悲恸揪心,尽表爱恨。但最后还是希望是个喜庆结局,不把眼泪感伤带回家去。但愿我们对待现实中曾经经历的悲剧,不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