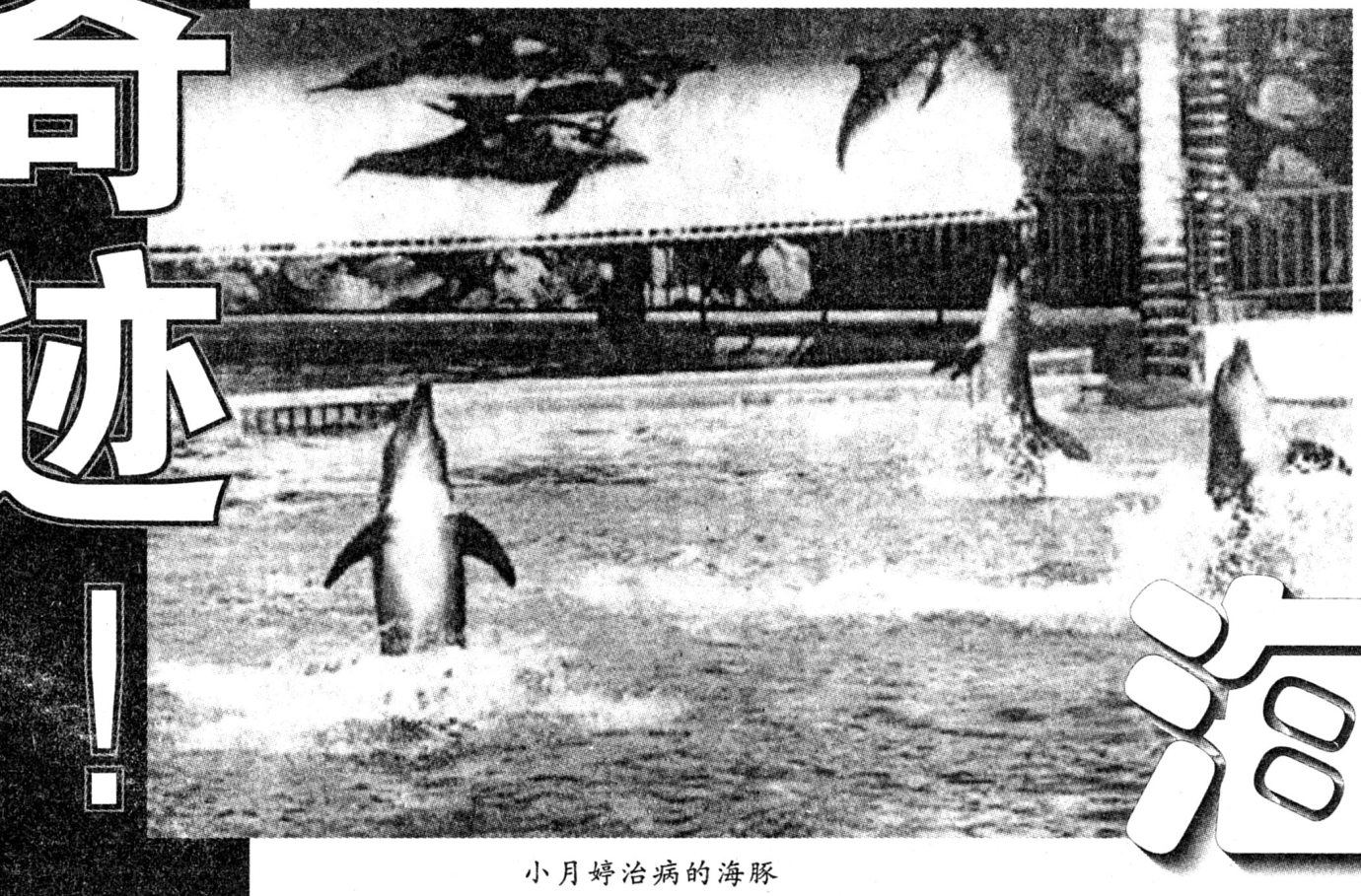□文/赵熙
刚入春三月,市面上各种西瓜渐多了起来。有海南的,台湾的,还有国外老挝,缅甸的。一打问,价格大约都在四五元一公斤。虽然是贵一些,但毕竟地处内陆的秦人可以吃到皮儿嫩绿光亮、瓜瓤鲜红多蜜的新鲜西瓜了。
一日中午特热,儿子胜买回半个绿皮红瓤大瓜,瓜味确也蜜甜沁凉,如我的蒲城故乡旱塬上了油渣的沙瓤瓜。这三月吃西瓜,实在是一种甜美的享受。
一家人饱餐一顿新鲜西瓜之后,我看见一盆吃剩的西瓜皮,忽然想起童年在老家镇子上拾西瓜皮,吃西瓜皮的日子。
我那故乡孙镇,每五日一集。在夏日里,从街堡到西关,乃至涝池岸畔的炭市、驴马市,几乎全是西瓜、梨瓜的世界。我和一群光身、赤脚的孩童,挎着八斤笼,或提小罐儿,挤在瓜市上,或拾瓜皮或捡瓜籽。母亲将干净一点的瓜皮,洗净削皮,或熬或炒,做出各种变样饭菜来。西瓜皮拌粉条、西瓜皮炒的瓜菜,烧的瓜皮汤,同面片烩的瓜皮“连锅面”。在那饥馑的年代,几把面片,半锅瓜皮,吃得又饱又舒服,确也省了粮。还有更好一些的吃法。将瓜皮条先在油锅炸了,调上蜂糖,浇了粉汁,锅中蒸了,则是一道有特味的蜜汁甜饭。我后来曾在榆林的友人家宴上,同样吃到了西瓜皮蜜汁的甜饭,那可是我至今难忘的一道塞上好吃喝。
其实,对农家人来说,西瓜皮也是喂猪的青饲料。我的胜、海儿在家乡的那年暑月,正值那头老母猪生了八九只小猪崽。老母猪食量特大。每到集日,七八岁的胜同五六岁的海儿便汇同村中六七个小同伴,挎上“八斤笼”去瓜市上拾瓜皮。孩子们有时为争得一片干净瓜皮,将吃瓜人团团围住,一个个小手儿几乎叠起来伸向吃瓜人的嘴边。弄得吃瓜人好笑而为难,看着这些日光下晒得黑赤溜溜、光头沁汗、黑眼睛直瞪瞪地盯着瓜皮的孩子,干脆猛咬两口,将瓜皮扔到笼筐里了,便逗得孩子一阵哄抢和嘻笑。我那胜儿一个集就能为大母猪拾回四五笼“瓜皮”。海儿年幼,挎不动瓜皮笼筐,用一根带尖钩的铁丝,钻在瓜车下,或驴蹄边,用铁丝勾那小瓜皮。挑上一片,便高高举起,如挑着一片月牙儿旗帜。进得屋门,高声尖叫,好像凯旋而归的将军。在后院晾晒瓜皮的父亲,喜得胡子上都挂着笑,“啊呀,我海儿能拾柴柴了。”
想起这一切,我的心便灼热兴奋起来。我自入古都,虽然整个夏日都有吃不完的西瓜,但却很少吃到瓜皮菜和瓜皮饭。我似乎从哪册杂志上读到,说是瓜皮的营养成份,包括“维他命”、微量元素之类比瓜瓤还丰富。于是,在这三月第一次吃到西瓜之后,我便极想吃母亲从前做的西瓜皮汤菜。我便将吃剩的瓜皮削净,切成薄片。在我忙着切瓜皮时,引起了三岁多的小孙女的好奇。她的眼睛刚刚能挨着案板楞边,便定睛地看,不住地问,“爷爷,你切瓜皮做啥?”
我说:“爷给你做瓜皮菜,又香又甜。”
小孙女便迫不及待地等着。当我在油锅炒着瓜皮菜,又加糖加酱油、姜、椒等红烧时,那特殊的瓜皮香便弥散开来,小孙女跑来跑去,大喊大叫:“吃瓜皮了,吃瓜皮了!”我从锅里夹了一小片,喂在她的小嘴巴中,尽管烫得她不住咧嘴,却一连吃了三条。吃晚饭的时候,因为多了一大碗红烧的西瓜皮,小孙女就米饭连吃了两小碗。夜里一家人看电视又吃西瓜时,小孙女特意将自己吃的一片小瓜皮悄悄地放进冰箱里了。张着黑豆豆眼,认真地对我说:“爷,瓜皮不能扔,再做瓜肉肉菜。”
谁知老伴夜里将吃剩的瓜皮全倒进垃圾筒。第二天一早,有了心思的小孙女,先去拉开冰箱,不见了她冷藏的那片瓜皮,又看见瓜皮扔进垃圾筒了,便一下大哭起来,含着泪向我告状:“爷,谁把瓜皮倒进垃圾筒了?”闹得全家人都在哄她,“再买瓜,不乱扔瓜皮了,全都给我乖乖吃瓜皮肉。”
小孙女终于泪花花地笑了。我冲胜儿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胜儿反嘴说:“有其爷必有其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