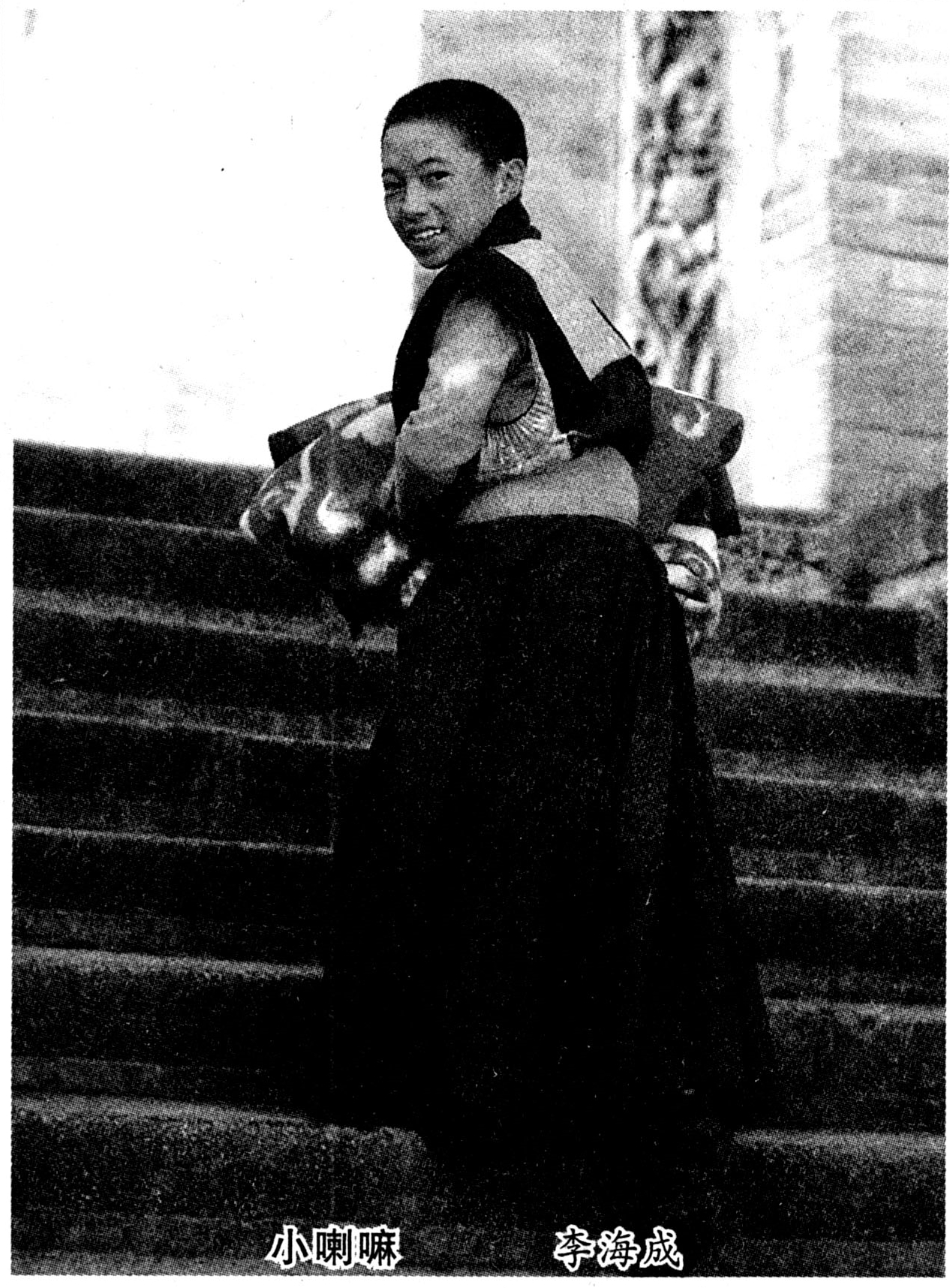□文/跃峰
多年了,补丁距离我的生活一直是忽远忽近。每每想起,昔日那些缝缝补补的日子便会纷至沓来。
记得小时候,左邻右舍有几个小姑娘,功课做完了,常围在母亲们身边,手里捏着一只鞋垫穿针引线。母亲们一边说东道西,一边侧过身子来指教,见有针脚走样的,会厉声训斥几句,偶尔也有打手板的,声音很清脆。因为在众人面前挨骂受训,小姑娘的眼泪流得特别快。见小姑娘抹眼泪,这时会有声音凑过来故意逗乐:“不会做针线活,长大了可就没人要啦!”小姑娘听了,哭得更加伤心。她这一伤心,惹得母亲们笑哈哈乐成一片。
多少年了,老家农村一向十分看重姑娘的手艺,打心眼里认为,针线活做得好的,定是心灵手巧者,长大了寻婆家时就多了一份优势。从小学做针线活便成了姑娘家必修的一门家庭作业。事实上,凡是后来针线活做得好的姑娘,举手投足间总透着一股灵气。有时想想,这也是一种必然,针线活里有花草虫鸟,打交道时间久了,自然颇受熏陶。
一手好的针线活,大多是用来打发婚后缝缝补补的日子。别小看这补丁,手艺高的媳妇,手工缝织的针角细密平整,与原样布料难辨真伪。在乡下,看一家女人,就看男人身上的补丁,普普通通的一块小补丁里,往往承载着女人全部的心灵和脾性。记得那阵子,每到夜晚母亲总是坐在炕头忙碌着缝缝补补,花花绿绿的布头摊开一大炕,母亲一边埋头翻找,一边和我们拉家常。钻在热烘烘的被窝里,我常惊讶母亲积攒的布头花样之多,无论什么样的衣服破了,母亲总能很快找出一块颜色一致的布块来做补丁,补丁似乎成了母亲辈们努力支撑和改善生活最无奈的一种力量。
那些补丁,现在很少能够看到,偶尔见到一两片,也是做工考究,随着新衣一块成形,已明显成为服饰上的一种点缀。即使眼下在乡下打工者身上,也很难找出一块补丁来。前两日附近的旧楼动工,一帮民工起早贪黑地打墙拆楼。我站在路边,寻摸了足有半个时辰,才在一位中年人的膝盖处发现了一块小补丁,发现的那刻,心中顿然涌出一股久违了的感动和惊喜。眼看着那方补丁欢快地在工地上跳动,我站在风雪里久久不愿离去。
补丁已渐渐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奢望。有些年头了,我再也没瞧见一次缝补了。记得有次母亲来我这里小住,见小孙子上衣袖口处有块破洞,唠叨着要找块布头缝补一下,翻遍了大橱小柜,也没找到一块补丁。末了,母亲遗憾地说:现在的家庭什么都不缺,就缺补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