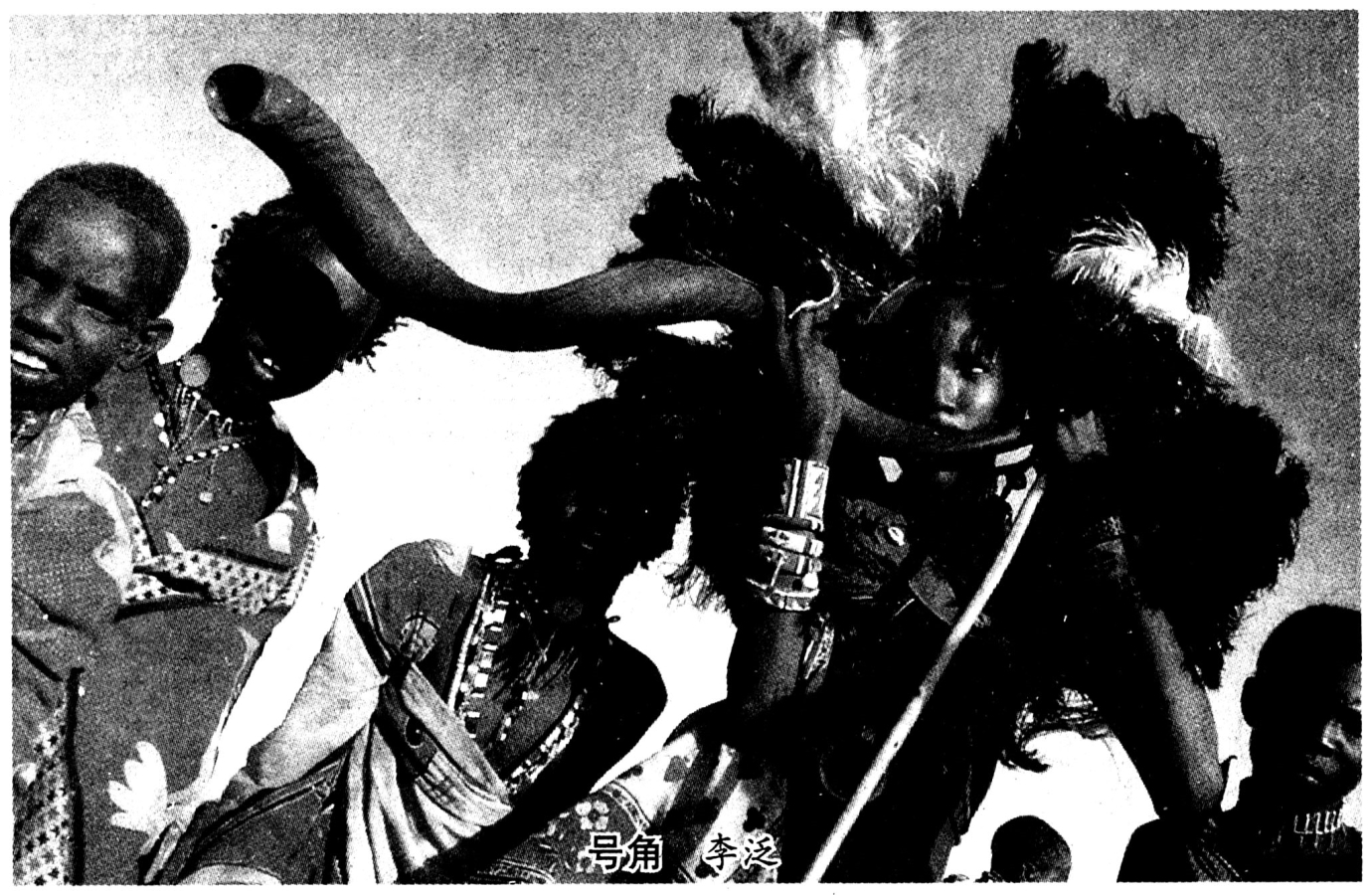文/老柯
日前,与一位曾供职县剧团的老兄闲聊,问及一位名角现状,不料对方讶然道,他已病逝数年,你不知道?我闻之黯然,良久无语。进入市场经济后,县剧团日益不景气,最后只能靠每人一月一二百元生活费混日子。对戏曲舞台的普遍衰落,这是大势所趋,区区一县剧团更是回天无力了。演员们老的老,走的走,改行的改行。我的那位名角朋友虽没离开剧团,但也没戏可演了。当地农村办丧事讲究“喧荒”(相当于过去的堂会,但以清唱为主),为了谋生,也顺便过把戏瘾,这位名角和几个师兄弟便干起了这行当。后来听说他们发展业务,把舞台上那套红白喜事的礼仪、程序,加以改造,注入现代生活内容,搬到农村红白喜事中,居然很受欢迎。那位名角也做了专职司仪。因他当年在《红灯记》中扮演的李玉和很成功,影响大,故而那些事主向人夸耀说,娃的婚事是请“李玉和”主持的云云。
不过,这位“李玉和”文革中还被劳动改造过。我当时正上初中,却不读书,整天跟着高年级同学“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天县城街道上,又多了一批正在扫街的“牛鬼蛇神”,其中一个有点眼熟。他个头不高,肩阔腰圆,抬脚动步显得与众不同。尤其是那双浓眉大眼,毫无其他“牛鬼蛇神”猥琐样子,反倒一派满不在乎甚至好玩神色。咦,这不是《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么?我们曾有一面之识的。他也认出了我,冲我挤挤眼,把戴在臂弯处的白袖圈朝我亮了亮——我看清上边用黑墨汁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几个字。后来,我才得知县剧团被一个管道具的夺了权,他因讲了几句不满讥讽话,遂被打为“现反”。但不久由于“革命工作需要”,他又唱起李玉和。再后来,由于两派群众组织武斗升级,他所属的那一派被赶出县城,以毛泽东文艺宣传队形式,到农村演出。我此时成了“逍遥派”,也就随他们游逛了一段时间。
宣传队所到之处,有同一派的群众组织负责接待,管吃管住,晚上演出结束后,还有一大锅煮面条伺候着,算是夜餐。往往这时,他都显得格外兴奋、活跃,并招呼我道:吃!快吃!这饭不要钱的。他自己连吃三大碗面后,还会再加一两个馒头的。见我惊异地注视他,他眼一挤,笑笑,照吃他的。有天不知为何谈到吃,我才知道他能吃的原因。60年代初,县剧团曾带着《王逵负义》等代表性剧目进京汇报演出,并在西北数省巡演。时逢困难时期,舞台上出尽风头的他们,却常常下台后饿得肚子咕咕叫。一次,竟偷偷捡来人家丢弃的白菜根煮了吃。不过,有次到部队驻地慰问演出后,大家美美吃了一顿饱饭。有的人一下子吃了11个馒头,把在场官兵都看愣了。更有趣的,是一位拉二胡的老艺人,因是盲人,部队特派个小兵伺候他。老艺人吃完一碗米饭,小兵给他再盛一碗。这么一碗碗吃下去,后来小兵干脆把盆端来,老艺人吃着,他不断一勺勺添着。等老艺人放下碗,一盆米饭也底朝天了……
记得当时听这个故事时,我哈哈大笑起来,他却没有笑。后来我明白了,这个故事里其实饱含着悲酸。文革之后,他又重登舞台,在《游龟山》等传统戏里担当主角。可惜我都没有去看。现在,也永无机会重睹他的舞台风采了。哦,那场风花雪月之事,只能留在我的记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