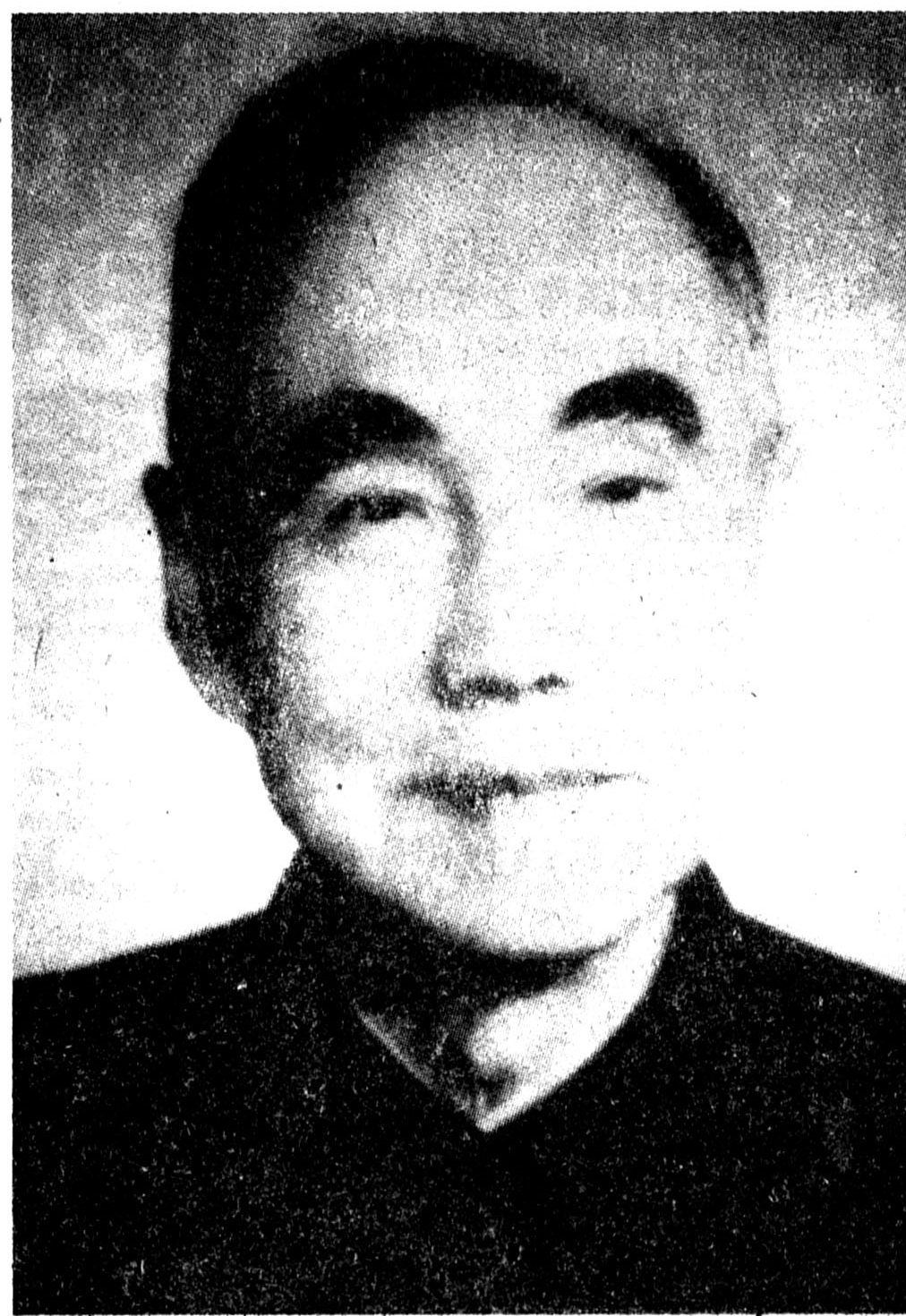□杨乾坤
忽一日,刘鉴兄来电,言其新闻作品已编辑成帙,命我校之。疑怪昨宵春梦好,今可先读友人之文,快战快哉。
此书名《刘鉴新闻作品选》,为其当记者二十余年代表性新闻作品之结集,凡二十万言。新闻三昧,以及表现之手段,刘鉴每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见意态随出。
刘鉴聪颖好文,却不道时也命也。他上中专,家遭巨艰,又逢国遭“文革”大难,1968年他毕业后,被入了另册,到了宝鸡水泵厂。后来,传道授业解惑,教了中学;再后来,便效法邹韬奋,一人编起《宝鸡科技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慧眼识珠,刘鉴当起记者来。
记者一途,诸多辛劳,因为当歌者歌之,当捅者捅之,当扶者扶之,当戒者戒之,眼观六合,耳听八方,然后咀而嚼之,匠心运之,及时作之,方可成文。二十年间,刘鉴的三千篇新闻作品风行三秦,流韵海内,难矣哉!
其为文也,有精意制作者,有妙手偶得者,有信手拈来者,更有呕心沥血者。他驻站宝鸡,终日孜孜,故而宝鸡十二县(区)之新闻报道,他是疏而不漏。奉命作全省重点稿件之撰写,也不辱使命。所见其言也真,其情也真,真心颂扬先进,鞭挞丑恶,思路敏捷,文气沉雄,凡行文皆于世而有益。
观《半个鸡蛋的透视》,知官员欺上瞒下之弊;观“‘3·12’案件”和“中国城夜总会拒检案”连续报道,知恶风之害;东岭村的成功典型,多少人受到鼓舞;杨清漪不屈服命运的向上精神,又感动得多少人泪眼朦胧。李秀英、王大中,真正民族之脊梁;田建国、谌宝,可歌可泣的人民公仆。至于原眉县县委书记马根旺和原宝鸡市民政局局长茹小魁的受贿案,刘鉴剖而切之,入情入理,影响巨大,非大手笔不能为也。日所思,夜所梦,敬业已到痴迷之程度。惟其痴迷,其作品便红了西府,红了陕西,名噪全国。因其思想新锐,下笔千钧,故而受到省委书记和省长的赞赏,受到海内不少媒体的青睐,受到中组部的赏识。
刘鉴自幼聪颖过人,自小就有文学梦,上初中时,他就在写一部小说。每晚上完自习,同学们就寝,他却独自一人在教室点起煤油灯辛勤劳作。此是我亲眼所见,不敢有杜撰的成分。那时同学们对他是仰而望之钦羡不已。谁知梦正酣,却祸从天降。1965年下半年,何物“社教”肆虐。解放十六七年了,“社教”却搜着寻着打着压着生拉硬拽着无中生有着,硬是给一大批农户补定了“地主”成分。多少人罹此“功德”而血泪斑斑!刘鉴和我同一大队,又同罹此祸。紧接着,又是“文革”,一祸既来,一祸又至,祸上加祸,民何以堪!
“文革”中,我俩有家难归。“文革元年”后的第二个春节,刘鉴寞然从宝鸡来,我凄然将其接到宿舍,兄弟独相对,心中惟苦悲,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就在那最黑暗的时候,刘鉴的母亲摸着刘鉴的头说:“娃呀,心要放宽,这世事是转的,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哩!”我的母亲也拉着我的手说:“前头的路黑着哩,谁也不知道咋走呀。”富有哲理的此等语言,不是出于伟人之口,却出于我们文盲的母亲,我们感谢母亲!
天旋地转,刘鉴鬼使神差调到了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当了记者。此后的二十年间,便是代民立言。尝记得1987年,扶风法门寺地宫惊现,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于是刘鉴邀叶广芩与我同去那里开了眼界。随即,刘鉴示我有关法门寺及地宫文物的稿件五篇。篇篇珠玑,读之令人余香满口。叶广芩与我遂将之编辑成法门寺专版,在《陕西工人报》发表。当署名时,倒也有趣。因五篇文章出自一人之手,而署名当有别。我便为其署名曰:刘鉴、天印、明镜、刘四、邶缑仁。天印是刘鉴的曾用名,明镜是其笔名,刘四因其在兄弟中排行为四,邶缑仁者,乃因其为北缑村人,遂取谐音之故。此谐音众人皆不知,后来我述之北缑村才子缑稳贤,他拊掌而笑。叶广芩又言,刘四不如再用谐音刘寺,我欣然从命。刘寺写法门寺,壮法门而事留也。
刘鉴的重要通讯,不少经我手而见诸《陕西工人报》。其大作告我时,有急如星火者,有持成稳重者。最难忘,关于田建国的通讯,煌煌八千言!为了时效性,刘鉴从宝鸡专程来西安送此稿件,午后两点,门前见面,随即安排他在饭馆进餐。两人面对面,他吃饭,我看稿,他扯面一碗,我陶醉其文,如此这般,饭吃完,稿看完,随即送审,稿件随即见诸报端。
二十年的奋斗,刘鉴成了高级记者,成了省劳模,成了有突出贡献专家。文学梦移至新闻,梦已成真,亦趣亦雅。今日结集的其新闻作品,富瞻博厚,沉雄而旷达,欲欣赏其文笔者,欲观瞻其思想者,请读此书。读此书而不掩卷三思者,当几稀矣。有感于此,因题五绝一首云:“秉笔立民意,风流自可亲。昂然向上路,天道正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