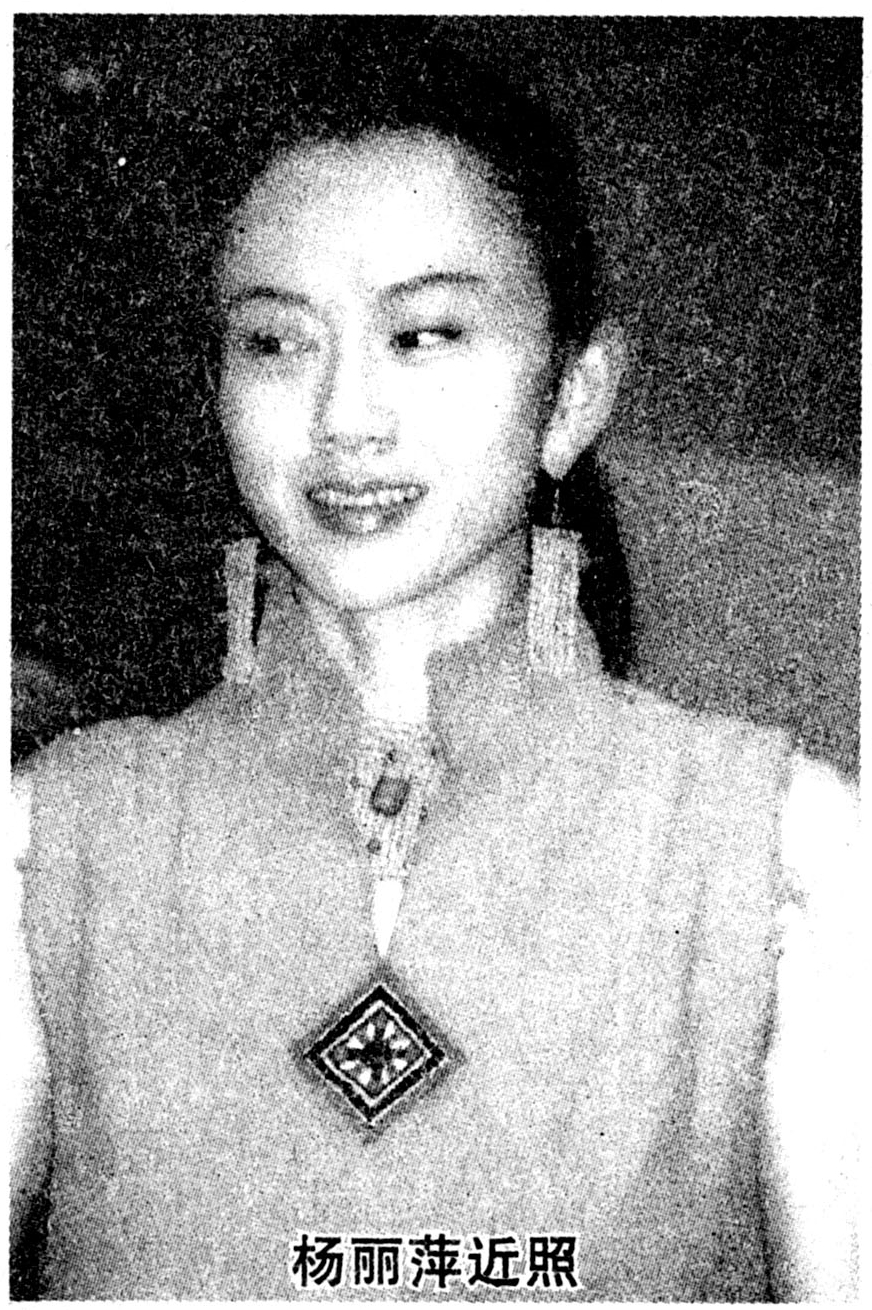□文/王如明
有人说读书要“博”,有人说读书要“精”。说要博读的如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庸》所言,人要“博学之”。说要精读的如宋代朱熹建言:“泛观博取,不若熟读精思”;有时即使在一个人嘴里,却初现似乎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如明代的胡居仁既说“学贵博”,又说“知贵精”。矛盾吗?其实一点也不矛盾,世上许多事情本就是对立统一的。
哲学中的命题很多,其中就有一个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命题。首先是“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这好理解,数量是基础,舍弃了数量何谈质量?反过来说,“没有质量就没有数量”,所以哲学中的数量与质量和读书的“博”与“精”都是相对而言,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所以才会出现古人似乎矛盾其实并行不悖的读书理论。不仅古人,今人同样有绝妙之论:鲁迅就说书要多读,“必须像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而邓拓却在《燕山夜话》中说:“读书不必求多,而要求精”。看似矛盾,但理解其精髓要义,“博读”与“求精”并不矛盾,是相辅相成、相反相成。反过来说,一个人抱着一本书精读百遍,即使倒背如流,也未免会眼光狭窄;个人博览群书,业无专攻,读无所获,只会成为一个“书袋子”。所以我赞赏博读与精读相结合,博读以防毁于偏,精读以防毁于随。有人说,哪能呢,人精力有限。其实借口没功夫读书都是一种托词。“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你要挤,就有;不挤,就没有。如果我们总觉得自己在知识的海洋中处于无知,就会像大学问家苏格拉底那样虚怀若谷——“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而拼命读书;如果不想读无所获,就要牢记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中国儒家经典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以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都是讲的博与精、读与思的关系,可谓治学良言。
读书,精于勤,荒于嬉,成于思,毁于随。只要意志坚定,形成良好读书习惯,且注意学习方法,会收获颇丰的。不信,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