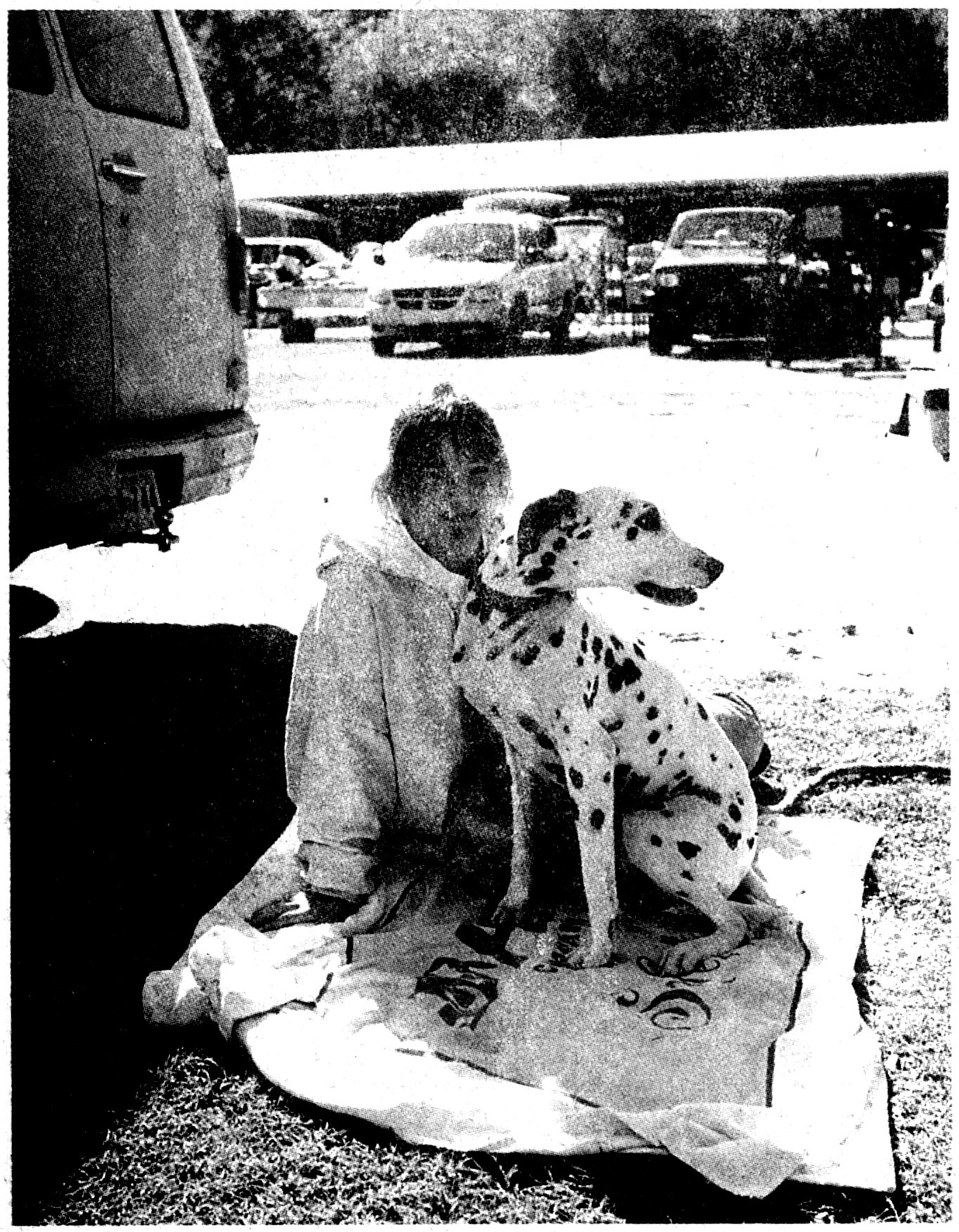[延安] 轶名客
路,一条普通的山间小路,从北方一座简陋的农家小院伸出,绕过屋前篱笆,跨过淙淙小溪,爬上高高山岭,弯弯曲曲,曲曲弯弯,一直通向远方……
1971年秋季,13岁的我背着母亲打点的破铺盖卷儿和五升口粮米,第一次远离家门,沿着这条山路,到十多公里外的桑塔中学求学。那年月,北方乡下人的生活是极其困苦的,勤劳淳朴的庄稼人,含辛茹苦地劳作一年,还得不到饱饭吃,买不起点灯油,往往靠树叶、野菜、细糠来充饥。至于学校的生活那就更苦了——每天两顿饭,而且每顿最多也不过两勺红高粱糁糁饭,只能吃个半饱。白日,许是紧张的学习不允分心,时光倒也勉强可以打发;可是一到晚上,尤其是那倒霉的漫漫冬夜,肚子咕咕地叫个不停,搅得人六神无主,实在撑不住了,就冲一碗盐开水充充饥。就这样,就算熬完了第一学期。
到了第二年春上,家中实在是挤不出多少口粮米了。为了不荒废学业,我决定“跑灶”(走读)。学校早晨七点半上课,十多公里崎岖不平的山路,途中还要翻越两座大山,至少要跑一个半钟头。每天鸡叫头遍我就起床,胡乱地扒上几口饭,揣上两块头天晚上母亲就烙好的苦菜拌高梁面饼子,便匆匆上路了。晨风飕飕,繁星点点,四周黑幽幽的,一片静寂,远处不时传来猫头鹰的怪叫声,使人毛骨悚然,不敢前行。这时,母亲便提了灯笼,踮着小脚,把我送上山巅,说:“只管大胆地朝前走吧,我照着你呢!”当我转过一个山弯,回头远远望见空旷的山路上母亲的身影和那跳跃着的灯火时,周身顿时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脚步也似乎迈得更快了。
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那时候山里庄户人家大都没有钟表,计时往往靠日月星辰运行来判断。有时早晨起冒失了,母子俩爬上山岭仍不见天亮,便常常在垴畔山上的场里小憩。一阵寒风吹来,冷得人浑身打颤,母亲便拾柴禾,点燃一堆篝火,给我讲起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星的童话故事。天幕上密密麻麻的星星与地上的篝火交相辉映,我的周身便暖融融的,不时地仰起头,仔细地寻觅着属于自己的那颗星。
命运之神往往捉弄那些苦难而善良的人。就在我为自己能勉强填饱肚皮得以上学而庆幸时,不料曾被胡宗南匪兵打坏一只胳膊的父亲,在一次放羊的归途中从山崖上跌了下去。望着躺在炕上呻吟着的父亲,想着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就要落在母亲一人身上,我的心犹如刀绞般难受,便产生辍学的念头。当我噙着泪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后,我至今还记得她老人家当时那痛楚的表情:只是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一动也不动;末了,又猛地将我紧紧地揽在怀里,全身剧烈地抽搐着,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经过一天一夜的思考之后,母亲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我继续上学的决定。为尽量减轻母亲的负担,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忍着饥饿,拼命地砍柴、割草、挖野菜。紧张的学习,加上超负荷的劳动,累得我头晕眼花,精疲力尽。有一次,本来就极度虚弱的我,连累带饿昏倒在山里。等我苏醒过来后,太阳已经落山了……
一种伟大的办量,鼓舞着我终于完成了初中两年半的艰难学业,走出了那条弯弯的山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