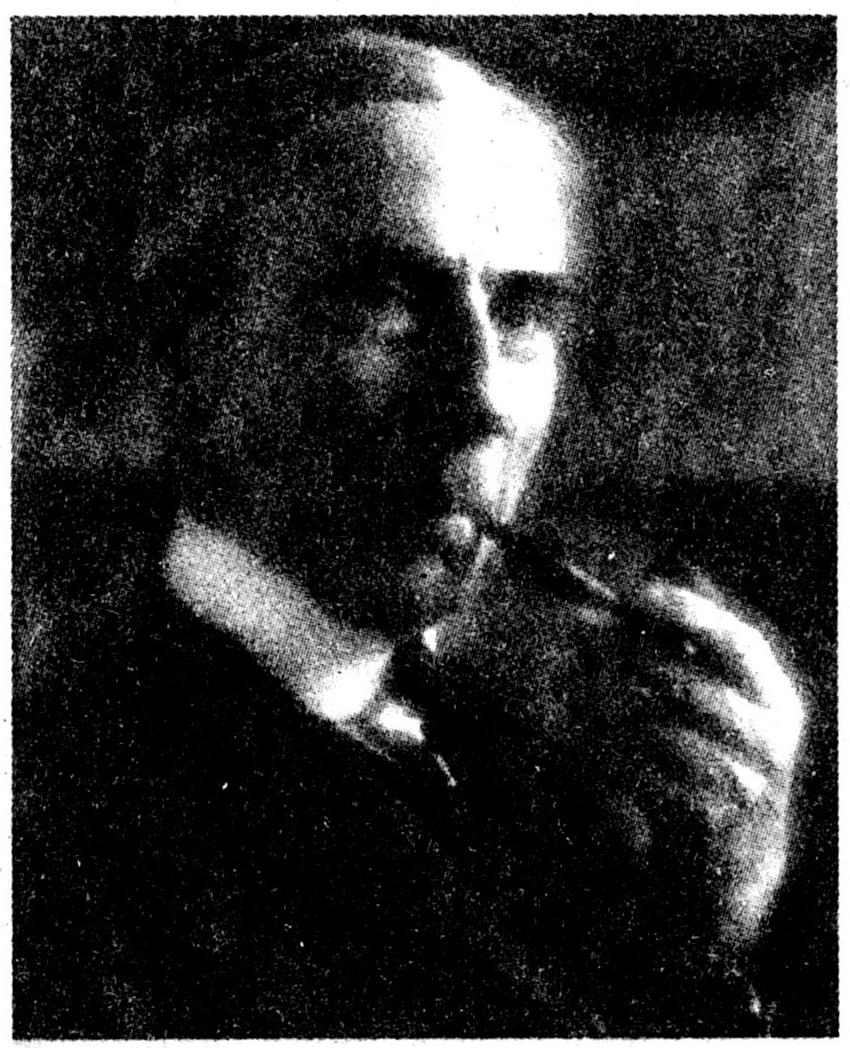□文/柯喜堂
无意收藏,却攒了一大纸箱小人书。其中有成套的《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文学名著,也有《保卫延安》、《平原枪声》之类红色经典。外国传世之作,像《上尉的女儿》、《伊利亚特的故事》、《奥德赛的故事》、《伪君子》等等,则是我的心肝宝贝,轻易不肯示人的。当然,更多的是童话和民间故事,这是儿子小时最爱看的。
不过严格地说,这些小人书都是上世纪80年代左右买的。而伴随我童年时代的那些小人书,则一本也没有留下。或许正是出于对这一遗憾的补偿吧,我以儿子的名义(当时他只有五六岁),逛书店总不忘选购一些小人书。到外地出差,带给儿子的礼物也多是小人书。那段日子可谓我的购书黄金阶段:一方面经历了十年文化禁锢之后,那些重新面市的中外文学名著不啻久违的美餐,惹得人满口津液,不惜倾囊一顾了;另一方面,当时书价不贵,如一套十六卷本精装《鲁迅全集》只卖50元。三大册精装《太平广记钞》仅售10元。至于小人书,也就一二角钱而已。我当时工资400余大毛,挤一挤,买书的钱还是有的。据说,疯狂购物是现代女性的一大快乐。如是,尽情买书,自是彼时吾辈快乐所在了。何况,买书、读书,尤其是翻阅那些以传统线描手法绘制的小人书(其中不乏大家之“小作”),不仅是读倦“大部头”后的一种精神调剂和休息,且在艺术享受中,唤醒童年记忆。从苍苍茫茫尘世庸碌中,擦洗出几分灿烂童心呢。小时家里贫穷,父母给的零花钱极少。偏偏上学路上有家新华书店,隔着柜台的书架上,总有透着墨香的小人书摆出,令人眼馋不已。一次,发现新上架一本《说岳》小人书,勾引的我这天连上课也没心思。在同学手里借到钱后,我利用下课10分钟时间,一路狂奔到书店——书是买到手了,却因误了上课时间挨了老师一顿批评。不过,放学后捧读那本小人书的陶醉满足感,足以抵消一切不快了。
我家住在小县城一座大杂院里,却非方方正正四合院,而是坐西朝东一字排开七八间厦子房,分住着三四户人家。紧挨东邻墙下是条长长的排水沟,使原本逼仄的院庭愈显得狭窄。不过,我却非常喜欢这条排水沟:盖用砖镶箍的沟沿,不少砖缝间,竟还嵌镶着厚厚小铁片!这一发现令我兴奋不已,抠出这些铁片卖给废品收购站,不就有了买小人书的钱么?这么想也就这么偷偷干了。挨大小骂自然是少不了,却也值。后来,我还摆过小人书摊,尽管获利甚微,却也多了“周转资金”,能够购买更多小人书。家里当时有个废弃的破风箱,遂成为这些小人书安身立命之所。可惜这些小人书后来星流雨散,一本也没留下。留下的,只有那份童年的温馨回忆而已。
与我相比,儿子的童年是幸福的。他虽生性爱好,有小人书看,他就老实安静多了。至今我还珍藏着儿子一张照片:小家伙坐在地板上,由于专注而微蹙着眉头,正入迷地看一本小人书,身边还散落着几本小人书。一把玩具手枪,却被冷落一隅。其实更多时候,是我给他讲小人书。由于对故事情节十分熟悉,我往往并不拘泥书中文字,而是以口语形式,给书中不同人物配上“画外音”。有时儿子儿会按照他对画面的理解,充任其中一个角色,这样“配音”也就成了“对白”,父子俩一块走进小人书世界,童心碰撞,其乐融融!眨眼20多年过去了。儿子去南方工作也已数年。当年小人书亦风光不再,据说早被花花绿绿的卡通书取而代之。或许是自甘落伍吧,我对小人书亦然情有独钟。不仅喜欢小人书那种简约醇厚的朴素美,从中翻出的,还有绵绵细细往昔岁月或生命的感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