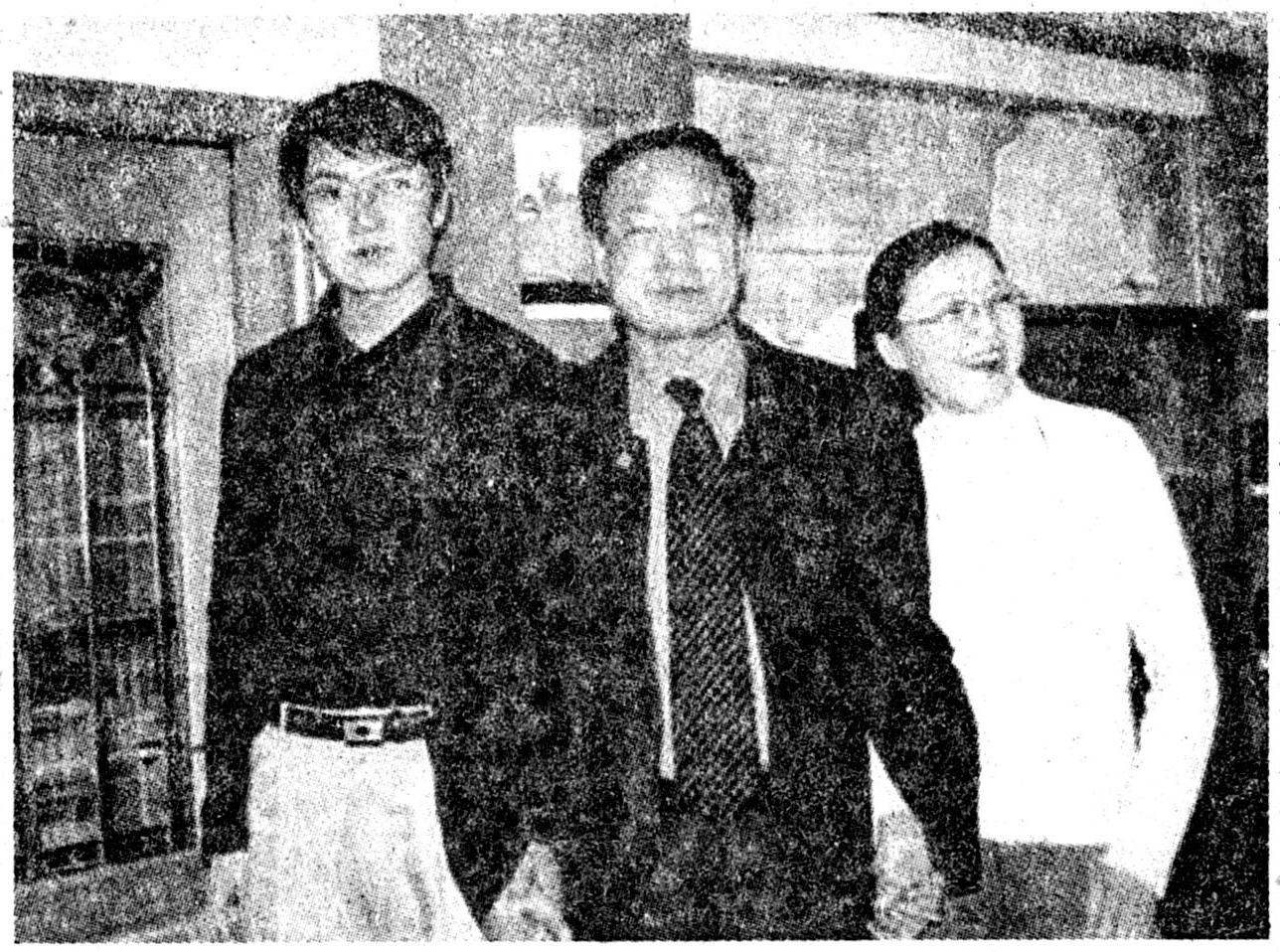□文/屈超耘
有人把读书的事看得太偏、太绝对,认为所谓“读”就只是“青灯一盏”地皓首穷经。其实,读书的方方面面很多,几乎可以用“百花齐放”形容。今天我所说的“谝读”就是这百花中的一朵花。
“谝”这个字比较生僻,一般人不常用的。《辞海》上解释说,它是花言巧语,或者是夸耀,显示,如“谝能”。要说,这只是一义。在陕西人的日常用语中,它是褒词,这是另一义,是作无拘无束地侃侃而谈或淋漓尽致、表达个人意见解的。友朋相遇,道合志同,毫无遮拦地交谈,用一个“谝”字,便有了声,有了色,还有面部喜悦的表情,手势的舞动,显得十分传神和生动,很得劲的。我很喜欢这个字,便常在电话上给老友们说:抽空在一块谝谝吧,开心开心。也常听人议论那些口若悬河的人说:××真谝得美,我就爱听他谝。
解释完“谝”字,回头再来说“谝读”。谝读,就是约三二知己,在一块交谈各自的读书情况,或者说就是几个相好的,在一起开个小小的读书心得交流会。只因为这种会是私人性质的,且规模极小极小,故还是以“谝读”命名最为贴切,也最为得体。那么,“谝读”到底有些什么好处呢?根据我的经验,有三:一、能谝出真知。人常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由于平时的读书都是单独行为,所得就只能是一己之见,这种“见”,可能浅,亦可能偏。而当二三知己一起“谝”,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就可以深化认识。比如读清代大文豪方苞的名篇《辕马说》,虽然我在年轻时就接触过,也有印象,然仅仅停留在就马说马阶段,从来没有深一步想过。几年前,我约了几位朋友在寄寞庄里谝它,谝着谝着便不知不觉地深化了,大家一致认为:方公是“醉翁之意不在马,在乎人事之间也。”所谓的说“辕马”,实际是以马喻人,是说领导,用今天的话就是说“一把手”。这么一深化,我马上就感到方老夫子的见高识远,他几百年前讲的那个“将车者,其慎哉!”实际上是在告诉管理“一把手”的人,对他的选择,任用要慎之又慎哪!二、能纠正错误。说实话,任何一个读书者,哪怕是大学问家,都可能在读的过程中出错。不瞒大家,我因为从小只上过几年正规的学校,是个典型“石狮娃的尻子——不深”的人,读书过程中甚至连一些生僻字都不认识。对于南明时期写《燕子笺》的阮大铖虽然知道,但因为马虎,把铖字当钺字读。有一次,约几位老友在一起谝《桃花扇》,当脱口说出“阮大钺”时,大家轰然发笑,随之纠正说:念铖不念钺时。老天爷,一次闲偏,竟然纠正了我念错几十年的字,使我好感动哟!你说,这谝读重要不重要?三、能互相鼓劲。几十年来,每当我约朋友在一起“谝读”时,总能获得上进心。记得有一次和老田、老杨谝宋朝的秦桧害岳飞,最后取得的共识是:秦桧只是个执行者,真正谋害岳飞的是宋高宗赵构,如果说害岳之罪为十,秦桧只能负其三,其余的七都应赵构承担。这次谝,给大家的上进心不小,仅我就陆续写出《秦桧只是前台表演者》、《秦桧是个“泥娃娃”》,发表后很受读者欢迎。
正如前边所述,“谝读”有这么多的好处,故我在其中获得的乐趣自然很多很多。请想,或晴昼,或雨夜,或炎夏,或寒冬,几位知友相聚一起,边喝茶,边闲谝,谝的是同一题目即最近读了什么书、什么文章,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感想,有什么疑问,有什么诘难,想啥说啥,咋想咋说,然后大家各说各话,夏天忘了室内的高温,冬夜忘了屋外风雪;小小客厅,“你方唱罢我登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说到开怀处,会心一笑,满屋温馨;谈到交锋处,互不相让,唇枪舌剑,你争,他辩,甚至弄得耳红脸赤。然一旦得出结论,顿时蓬筚生辉,无异于中了头名状元那般高兴,真惬意的了得!
接受“谝读”吧,搞起“谝读”吧,我亲爱的读书朋友。如果一年能和知己朋友搞四五次“谝读”,十年就是四五十次,若能一辈子坚持“谝读”,那绝对会获很大的益。不信你试试,如果没有用处,我愿赔你的青春损失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