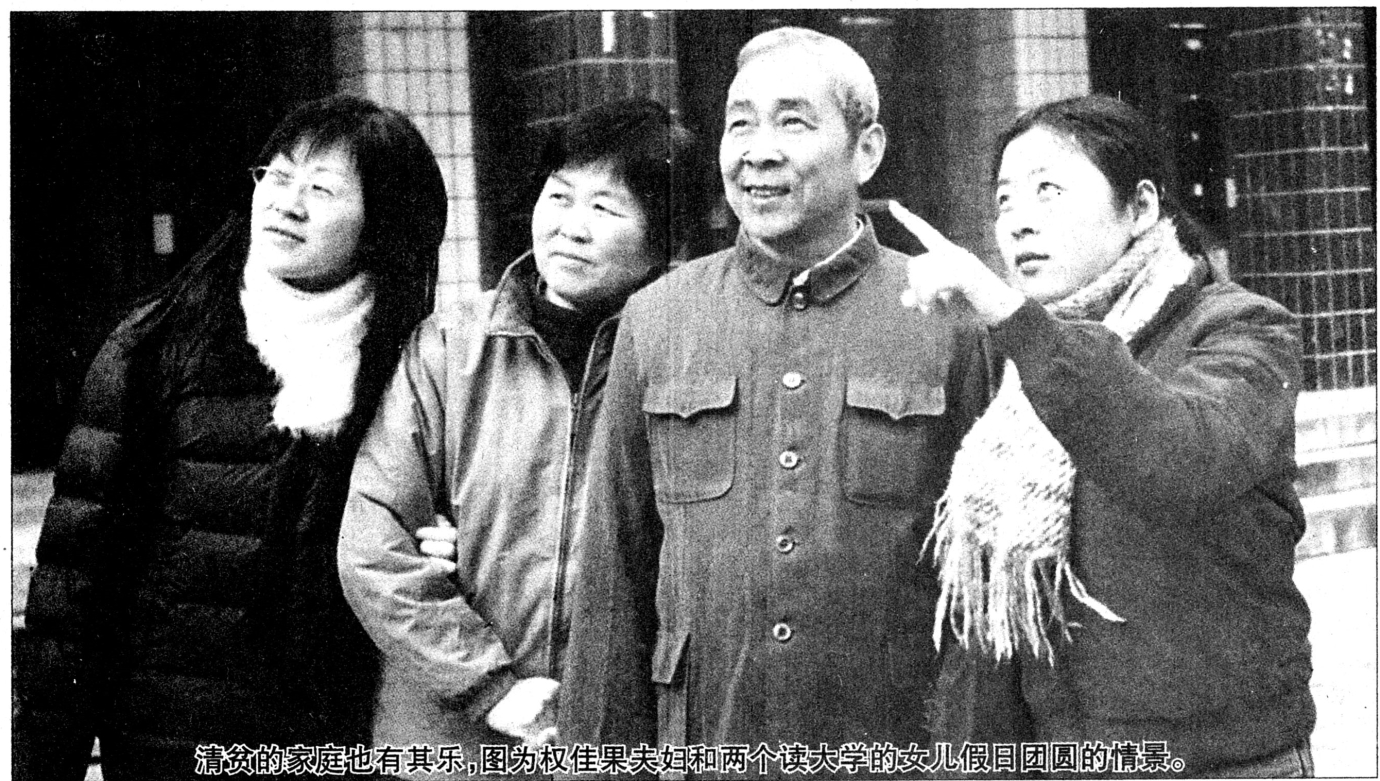舍命进京上书的民间思想家
1968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贾曲村初中辍学回乡青年权佳果,面对“文革”中出现的一大堆社会问题,用两年来自己钻研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体会进行观察思考,系统地将自己的见解写成《提交中共中央对社会的认识》一文。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灾难。指出:这场运动“不是教导群众理智,而是教导群众蛮横;不是教导群众聪明,而是教导群众愚蠢。”在文中疾呼:“现在的毛泽东思想,已被搞成面目皆非的东西。”“个人崇拜搞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怎样才能改变这种混乱局面,他建议党中央:“应该把力量集中到组织生产和生活上来。现在正是主要工作方针实行这个转变的时候了。”3月3日,他揣上洋洋5万言的文稿到了中央“文革”接待站,要求转交给中共中央。但立即被捕,关进监狱。审讯时他据理以争,认为自己写的材料不是反动的,是正确的,“无论判我什么罪,我保留意见,保留我对社会的认识。”同年12月,他被押回蒲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15年徒刑(1979年3月平反)。
(摘于《蒲城县志》附录:文化大革命纪略)
如此殉道者今日寥若晨星
据我所知,在当代中国伦理学界,权佳果可以说是个奇人。奇在他既非书香门第,早承家传,也非科班出身,名师指点,只是一个小学毕业的农家子弟,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仅凭自己的颖悟和执着,刻苦自学,闯进了幽深的哲学殿堂。奇在他心甘情愿作一名真理的探索者和殉道者,为此,饱受牢狱之难和贫寒孤独之苦,“虽九死而犹未悔”。别人用学问、理论为自己编织花环,他却默默地用心血浇灌真理的苗圃。不管政治高压还是金钱狂潮的冲击,都改变不了他关心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情怀。除了读书、思考、写作,似乎再没有别的乐趣。每次学术会议上,他那一身显得土气的中山装和不随大流的举止言谈,常给人留下木合时宜的印象。但他不为流俗所动,处之泰然,安享自己的那一份寂寞。这些年来,学术界热闹非凡,新作新论让人眼花缭乱。其实一些人不过以此为饵,去沽名钓誉罢了,像权佳果这样淡泊名利、苦心孤诣探求真理者,在当今商品社会可谓寥若晨星。
(摘于省伦理学学会副会长、宝鸡文理学院教授王磊为权佳果《中国伦理》一书作的序)
铁窗生涯未改赤子痴心
陕西渭南师范学院权佳果先生的《伦理学通信》一书出版了。《伦理学通信》一书就如同在听一位执着的求索者的诉说。该书的作者权佳果先生不是什么知名学者,但其品格和学说都不同凡俗。知识分子(尤指研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者)大致可分为三类:谋食者、竞技者和求道者。谋食者只是混饭吃的人,竞技者是要与同行一争高下的人,求道者则是努力悟道的人(详见拙文《谋食者·求道者》,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3期)。权佳果属于最后一类,这最后一类知识分子是最为执着的人,但也是最不为世人看重的人。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今天,能赚钱、能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人(即聪明且办事效率高的人)才受重视。在聪明人看来,求道是愚蠢的事情,求道者是最迂腐的人。今天的聪明人们若见了权佳果,一定会断定这就是一个最迂腐的人。十余年铁窗生涯似乎未改这位求道者的痴心。遭此一劫后,本可以务实一些,圆滑一些,但他却选择了哲学伦理学这种很没“用”的学科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根,而且其言说并无饱经风霜后的世故和圆滑。
如今著书立说者多矣,且不说明星们写的自传,光学术著作就令人目不暇接。但许多专家教授写的书都不及默默无闻的权佳果写的这本《伦理学通信》耐读。首先,权佳果是用心写作,是从自己艰难曲折的生命历程和呕心沥血的求索过程中总结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道理;而时下许多专家学者或者为完成一个又一个项目而写作,或者为晋升职称和报奖而写作,或者为出名而写作。其次,权佳果的语言功底很好,其表达琅琅上口富有诗韵,把深刻的哲理解释得深入浅出,全没有时下某些专家学者的那种故弄玄虚。最后,权佳果仍未失赤子之心,其言说尽情直遂,不像许多著作者(包括笔者)在写作时怀着种种顾虑,生怕触犯了什么禁区,更不像有些作者,本是为迎合某一类人的需要而写作,其表达就不免虚伪矫情。
(摘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庐峰为权佳果《伦理学通信》一书写的简评) (明烛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