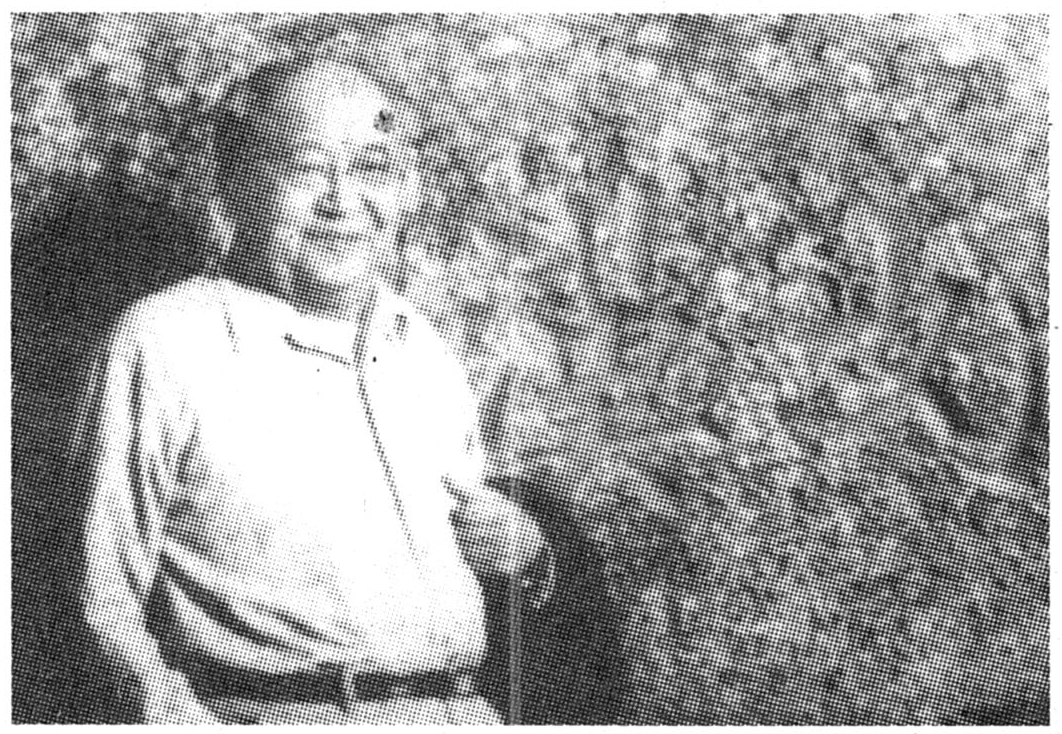郁建民
有时很奇怪,爱上某位作家的书,不管他的哪类作品,都一个劲地追着看。开始,我一惊,以为犯了“偏食”。后来,读了林语堂的《论读书》,心才定。嘿,瞎子摸对了路。
林老先生说,有人读书读了半世,亦读不出什么味来,这只是因为读不合味的书,及不得其法。读书须先知味,这“味”字,是读书的关键。所谓味,是不可捉摸的。一人有一人胃口,各不相同,所好的味亦异,正如英国有句名俗语所说:“在这人吃来是补品,在他人吃来是毒质”。读到了对味的书,找到了思想相近的作家,就像找到了“情人”,必胸中感觉万分痛快。袁中郎夜读徐文长诗,叫唤起来,叫复读,读复叫,便是此理。
林老先生还说,知道情人滋味,便知道“苦学”两字是骗人的话,学者每为“苦学”抑或“困学”两字所误。读书成名的人,只有乐、没有苦。旧时有人马背上读书、庭院里吟书、如厕时看书,大概是爱书至极。如果没有情人般痴情,何以如此形影难离?没有乐,读书效果会打了个折;苦读书,快乐也会大打折扣。
据说古人读书有追月法、刺股法及丫环监读法,其实都很笨。读书无味,昏昏欲睡,就拿锥子在股上刺一下,这是愚不可及的。不睡觉,只有读坏身体,不会读出书的精采来。刻苦耐劳、淬砺奋勉是应该的,但不应该因此而视读书为苦。
读书传雅意,书中藏乐趣。也许是我走了大半截人生路,才获得的一丁点之悟。